一 金庸生平与著作年表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生,浙江海宁人,出身望族。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大学主修英文和国际法。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曾在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及《新晚报》任记者、翻译、编辑,1959年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期间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1972年,金庸挂印封笔,金盆洗手。所获荣衔甚多,包括:1981年英国政府O.B.E.勋衔,褒扬其对新闻事业及小说写作的贡献;1986年香港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博士,表扬其对社会工作及文学创作的成就;1988年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名誉教授;1992年加拿大UBC大学DoctorofLetters;1994年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以及1996年剑桥大学荣誉院士等。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他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
1924 出生。
1932 8 读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此后对武侠小说日渐著迷。
1939 15 出版第一本书《给投考初中者》。
1941 17 因壁报《阿丽丝漫游记》一文被校方开除。
1944 20 考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因对国民党职业学生不满,向校方投诉而被勒令退学。在中央图书馆图书馆阅览室挂一职衔。
1945 21 在杭州《东南日报》任外勤记者。
1946 22 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被录取为上海《大公报》国际电讯翻译。
1948 24 被调派香港,续任国际电讯翻译。
1949 25 发表第一篇国际法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
1950 26 应邀北上赴京到外交部求职,但失望而归;并因此婚姻破裂。 不久,其父查枢卿被作为“反动地主”在家乡受到镇压。
1952 28 《新晚报》复刊,调任该报副刊编辑,并撰写影评、电影剧本。
1955 31 在梁羽生、罗孚等人影响下,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金庸笔名首次出现,一经《新晚报》发表便引起轰动。
1956 32 《碧血剑》开始连载。
1957 33 进入长城电影公司。写《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
1958 34 与程步高合导电影《有女怀春》。
1959 35 与胡小峰合导电影《王老虎抢亲》。 创办《明报》。
1961 37 《倚天屠龙记》、《白马啸西风》开始在《明报》连载。
1962 38 《明报》因报导“逃亡潮”而名声大噪,发行量遽增。
1963 39 《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连载。 发表《宁要裤子, 不要核弹》社评。
1964 40 与《大公报》展开一系列笔战。
1965 41 赴欧漫游期间,《天龙八部》由倪匡代笔。创办《明报杂志》。
1966 42 对“文革”做一系列分析。
1967 43 香港爆发“六七暴动”,《明报》成为左派分子重点袭击目标。
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创办《新明日报》。在香港创办《明报周刊》。创作《笑傲江湖》。
1969 45 创作发表巅峰之作《鹿鼎记》。
1972 48 《鹿鼎记》连载毕,宣布就此封笔。开始修订全部武侠小说作品。
1973 49 以《明报》记者身分赴台访问10天,之后于《明报》连载《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1979 55 台湾远景出版社正式授权出版《金庸作品集》。
1980 56 广州《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金庸武侠小说正式进入大陆。台湾远景出版社在《明报》刊出《等待大师》广告,征集金学研究稿件,之后出版《金学研究丛书》二十余册。
1981 57 与妻子儿女回大陆访问,会见邓小平,并游历13个城市。 获颁英国政府O.B.E勋衔。
1984 60 出版《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之一》一书。再次赴北京访问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85 61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86 62 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正式授权出版《金庸作品集》。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88 64 “主流方案”事件在港引起轩然大波,发表《平心静气谈政制》文章。获香港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
1989 65 宣布辞去基本法草委、谘委职务。在《明报》创办三十年庆祝茶会上,宣布卸下社长职务,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1 67 明报企业挂牌上市,并与其签订三年服务合约。 与于品海联合宣布:智才管理顾问公司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
1992 68 赴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于牛津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持讲座,作《香港和中国:一九九七年及其後五年》的演讲。回乡寻师访友,并为嘉兴市捐建“金庸图书馆”。获加拿大UBC大学 Doctor of Letters。
1993 69 发表《功能选举的突变》长文。赴北京访问,会见江泽民。宣布辞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职务,改任名誉主席。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一文,确定“退休”一事。
1994 70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金庸武侠小说第一部英译本。 北京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大陆简体字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名。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第一部生平传记《金庸传》在香港出版。
1996获英国剑桥大学荣誉院士。
1999受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职
……
金庸的作品包括:
1.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白马啸西风》、《鸳鸯刀》、《越女剑》。以上各书均曾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续剧、广播剧、舞台剧等,其中若干作品已被译成英文、泰文、越文、法文、马来文、韩文等在海外流传,日文版亦将由德间书店於1996年9月起陆续出版,其作品销路长期高踞华人社会之榜首。
2.政治评论:撰写《明报》社评二十馀年,有《香港的前途》评论集。
3.散文:有随笔、电影评论、戏剧评论、佛学研究及历史人物研究《袁崇焕评传》等。
4.翻译:已出版者三种,在报刊连载者四种。
5.电影剧本:十馀种,电影剧本《绝代佳人》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金章奖。
二 金庸生平研究
金庸的生平研究一直是金庸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三个原因:一是大陆的学术传统很少为活着的人列传;二是金庸很少提及自己的成长历程,除了在小说后记中偶有雪泥鸿爪,单篇成型的回忆性散文只有《月云》(《收获》2000年第 1期);三是大陆的传记作家因为地域的限制,研究金庸的生平多依据港台的二手资料,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这样的传记有《侠之大者——金庸评传》(桂冠工作室,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4年版), 和《金庸传奇》(费勇、钟晓毅,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等。即使是香港作家冷夏撰写的《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问世后也遭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如严晓星的《 〈文坛侠圣:金庸传〉 指谬》(《人物》1999年第 1 期 ) ,依据丰富的文献积累,随手就从《金庸传》中找出十余处明显的硬伤,包括金庸进入《东南日报》和《大公报》的时间,《明报月刊》的创刊时间等。
2000年以后,每年都有金庸传记出版,即《千古文坛侠圣梦——— 金庸传》(孙宜学,团结出版社 2001 年版),《挥戈鲁阳:金庸传》(彭华、赵敬立,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和《金庸新传》(艾涛,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2年版)。2003年 7月新出的傅国涌写的《金庸传》(十月文艺出版社),选择了平视的角度,坚持客观、中立、理性的立场。作者试图用平实的语言,忠实地再现金庸—— 一个作家、报人、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人生历程,写出一个真实的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傅国涌遍读金庸青少年时代生活、求学过的浙江海宁、嘉兴、丽水、衢州等地文史资料,还在浙江省档案馆爬梳出了不少珍贵文献,取得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所不足的是:因为条件限制,作者无法阅读包括《明报》、 明报月刊》在内的原始资料。
三、金庸小说研究
当香港和台湾在逐步接受金庸小说的时候,近在咫尺的大陆却是另一种景象。1979年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与港台的经济文化交流随即增强。1980年10月《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1981年广东科技出版社印行《书剑恩仇录》,揭幕了金庸小说在大陆的传播史。然而这种传播并非出自金庸本人的意愿,大多以盗版的形式,将印制拙劣的金庸小说塞满了城市和乡村。在1985年,金庸小说的盗版陡然达到了最高峰,金庸所有的小说皆得以和大陆读者见面,而且《天龙八部》有三种版本,《射雕英雄传》《碧血剑》《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各有两种版本。金庸作品在当时大陆究竟印了多少本,永远是个谜!某出版管理机构官员曾亲口对金庸说,1985年这一年金庸小说销售了4000多万册,几乎都是盗版。其中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经金庸授权发行了50万套《书剑恩仇录》,校印认真,并依据合同支付版税。在1985年第4期黑龙江克山师专学报上,张放发表了《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这是大陆第一篇金庸小说的研究论文。
面对突如其来的武侠小说热,大陆传媒延续了新文学工作者瞿秋白《唐吉诃德的时代》,郑振铎《论武侠小说》和茅盾《封建的小市民文艺》的理论口径,有人厉词声讨,斥之为“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有人如临大敌,提出应采取严正措施并有所防范;有人认为新武侠小说热,严重地冲击了纯文学,向纯文学提出严重的挑战,新武侠小说审美趣味低下。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红学家冯其庸出来为金庸辩护,他在1986年第8期的《中国》月刊发表《读金庸》,认真评述了金庸小说广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认为把研究金庸小说称作“金学”是有道理的。有一段时间,冯其庸的声音是寂寞的。到了1988年,《读书》《文艺报》《上海文论》等文艺类核心报刊分别刊登柳苏《金色的金庸》,章巽《台港“金学”一瞥》,裘小龙,张文江,陆灏《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等文章。而这一年,引起广泛争论的是文学史家章培恒发表在《书林》第11期的《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李自成》第二卷曾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代表了当时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而章培恒指出金庸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均高于《李自成》,前者“假中见真”,人物性格真实而富有感染力量,后者“真中见假”,导致读者的幻灭感。这是一次直率的发言,它第一次跨越了金庸小说自身的范围,而大胆介入大陆当代主流文学的领域。
金庸小说产生无数的话题,金庸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根本原因在于金庸小说有与众不同的魅力。金庸的小说,无论是立意的宏大深远,还是人物的多姿多彩,无论是结构的创新求变,还是语言的委婉动人,都可以和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相媲美。
在金庸小说研究方面,文字量最大的是陈墨。陈墨已经出版了 12 本关于金庸及其小说的著作,包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金学研究系列”7 种:《金庸小说赏析》(1990),《金庸小说之谜》(1992),《金庸小说人论》(1994),《金庸小说艺术论》(1994),《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1995),《金庸小说之武学》(1996),《金庸小说情爱论》(1996);上海三联书店的《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1999),《浪漫之旅——金庸小说神游》(2000),《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2001),《英华之咀——金庸四部佳作回评》(2002);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武林文宗· 金庸》(1998)。其中,《金庸小说之武学》、《金庸小说情爱论》在 1993年曾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分别为《金庸武学的奥秘》和《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
在陈墨之前,还没有评论家这样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金庸,陈墨又是性情中人,他的文章读来有天马行空、汪洋姿肆的快感。遗憾的是:作者行文不够简练,由于过多引用相同资料而带来阅读上的雷同感。陈骏涛认为,陈墨的研究有四个特点:材料丰富,自成体系,分析透辟,气势夺人,并批评陈墨文字“水分较多”。(《大陆“金学”第一家——— 陈墨和他的金庸及新武侠研究》,《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第 2期)应该说,陈骏涛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多是从综合考察开始,再分析单部作品,并兼及小说人物研究。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多综论金庸,如张颖的《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正邪一统观》(《蒲峪学刊》1988 年第 3期),唐解放等的《金庸启示录》(《鸭绿江》1988年第 6 期),张越的《金庸武侠小说中人物塑造的特点》(《上饶师专学报》1989 年第 1 期),黄振源的《铁血丹心,侠骨柔情——— 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小说评论》1989年第 6期),竺亚的《自古英雄出少年——— 金庸武侠小说及金庸谜一解》(《华文文学》1990年第 1期),虽向中的《“金庸”意境》(《书林》1990 年第 3期),宋文縯的《评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人文杂志》1991年第 1期),吴秀明等的《金庸:对武侠本体的追求与构建》(《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 2期),等等。上述论文对金庸研究有草创之功,但由于观念限制和资料缺乏,对金庸小说的分析只能是浮光掠影。
至 90年代中期,金庸从 80年代的匿名流行开始获得经典命名,对金庸小说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严伟英的长文《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认为,金庸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59年以前的小说强调救世思想,人物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处世;从 1959年的《雪山飞狐》开始,作品的批判性加强,时时流露出作者对丑恶人性的憎恨,并彻底反省早期不成熟的民族观念;1965 年至 1972年,《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作品分别采用反讽、隐喻、讽刺等手法,对人生和历史的没落进行批判,同时反映作者从过于入世的人生观摆脱出来,寻求朴素与自由的人生 (《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吴秀明、陈择纲《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一文,立足于时代转型和文学史的双重角度来考察金庸对武侠小说现代性所作的贡献,认为这种现代性是金庸以“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为基点,充分吸纳传统和民间的丰富养分,用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武侠文类的陈旧落后思想的一次革命性改造(《杭州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期)。吴秀明、陈洁的《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一文则认为,在金庸之后的“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面临严峻的挑战(《文学评论》2003 年第 6 期)。李癭《金庸小说论纲》(《鸭绿江》1995年第 1 期 ),孟庆林《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青年思想家》1995 年第 2期),李幸《金庸给了我们什么》(《鸭绿江》1995 年第 4期),鞠继元《论金庸小说与新神话创作》(《通俗文学评论》1997 年第 1 期),周泉《后风格错觉与语言致幻剂——— 金庸武侠小说的三重解读》(《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 2期),徐岱《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 4 期),徐岱《论金庸小说中的信仰之维》(《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 1期、第 2期),姚晓雷《金庸:都市民间舞台上的欲望舞蹈》(《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 5期),章隆江《论金庸小说的生命意蕴》(《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 1 期),朱寿桐《在与精英文学的比照中——— 再论金庸文学的通俗品性》(《论文集》)等文章,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金庸小说,值得一读。
北京大学在90年代逐渐成为金庸研究的重镇。陈平原在1990年就开设了武侠小说研究的相关课程,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准备和写作时间是1989年夏秋到1990年底。严家炎在1995年春为本科生开讲“金庸小说研究”,标志着金庸小说走向大学讲台的开端。严家炎根据自己讲稿整理而成的《金庸小说论稿》,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首先从文化生态平衡的高度研讨武侠文化的作用,试图澄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武侠小说的误解与偏见。全书综合而系统地考察金庸小说“义”,“武”,“情”的三维组合与作品的现代精神,情节艺术,生活化倾向,影剧式技巧,以及金庸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联系,并从文学雅俗对峙的角度衡定了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字里行间折射出一位文学史家的历史责任感。然而学院教授的热情推许,仍旧是持精英立场者对于大众文化孤岛进行的外在命名,并未完全打破雅俗文学的二元对峙。第一篇关于金庸小说的博士论文也出自北大,这就是宋伟杰的《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1997)。对金庸研究的用心,恰印证了北京大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术传统。
关于金庸的单部作品的论文还不多。有 2篇是讨论《书剑恩仇录》的,即张放的《〈书剑恩仇录〉的语言表现艺术》(《蒲峪学刊》1988年第 3 期) 和冯其庸的《论〈书剑恩仇录.〉》(《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 5期)。有 2篇是讨论《笑傲江湖》的,即计璧瑞的《试论类型——以〈笑傲江湖〉为例》(《论文集》)和董乃斌的《从游戏到消解——— 关于金庸〈笑傲江湖〉的议论》。(《论文集》)有 2 篇是关于《连城诀》的,即张健的《〈连城诀〉的主题、人物与情节》。(《论文集》)李爱华的《〈连城诀〉:贪婪人性异化的寓言》。(《语文学刊》2004年8月)还有 3 篇是分析《鹿鼎记》的,即席剑海的《〈鹿鼎记〉解读》(《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 4 期)、陈建新的《〈鹿鼎记.〉:成年人童话的消解——— 兼论金庸的现实主义倾向》(《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 4期)和骆寒超、骆蔓的《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兼论〈鹿鼎记〉的先锋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 5 期)。《鹿鼎记》这部“反武侠小说”,因为它的非武、非侠、非史、非奇,又有武、有侠、有史、有奇,被有的学者称作是一部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大百科全书,而《鹿鼎记》的主角韦小宝就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张明澍的《韦小宝现象》很早就开始关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自学》1989年第 11 期)。而王从仁通过分析韦小宝,发现中国文化的深层与其说是“儒道互补”,不如称“杨墨互补”,杨朱思想的核心为“为我”、“贵生”,墨子则为“兼爱”、“贵义”(《阿Q与韦小宝——— 兼谈中国文化深层的另一种影响》,《文史知识》1992年第 1 期)。陈墨则认为对韦小宝这一人物进行简单的道德审判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韦小宝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韦小宝形象的第一个层次是韦小宝被定位为一个“真小人”;第二个层次,即真小人的真实性及复杂性。《鹿鼎记》和孔子《论语》最能反映中国人的性格及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中国文化的精灵与怪胎——— 韦小宝论》,收入《孤独之侠》)讨论韦小宝形象的论文,还有徐保卫的《“鹿鼎公”的人格象征——— 金庸小说的自我意识》(《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 5期),陈尚荣的《韦小宝这小家伙》(《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 1期),姚晓雷的《当下市民文化精神的两种演示——— 王朔与金庸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比较》(《文学评论》2003 年第 1 期)和张目的《可疑的笑脸——— 话说韦小宝》(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年版)。郑锋的《说不尽的韦小宝——金庸〈鹿鼎记〉人物分析》。(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韦小宝这一艺术形象的文化内涵及其艺术价值,决难在一般小说人物形象研究中得到充分认识,“《 鹿鼎记》和韦小宝研究”,可能是金庸研究中的一个专门化分支。
一位成功的作家能留给读者的,就是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康序、陈颖灵的《此侠只应中华有——— 谈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主人公段誉》(《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 3期),是最早的金庸小说人物论。而关于金庸小说人物的第一种著作是曹正文的《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年出版,1996年由学林出版社出新版,增“范蠡”篇。以后的单篇论文有陈薇的《一曲人间悲歌——看金庸笔下的萧峰》(《通俗文学评论》1995 年第 2 期),陈墨的《虽万千人吾往矣——萧峰论》(收入《孤独之侠》),周志强的《论萧峰形象的文化蕴涵》(《华文文学》2001年第2期),陈墨的《段誉形象及其意义》(收入《孤独之侠》),陈墨的《不识张郎是张郎——张无忌形象散论》(《论文集》),黄立华的《浪子的颂歌—— 令狐冲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 年第 4 期),龙雍生的《萧峰的儒家之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董瑞生的《环境、性格、命运——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语文学刊》2005年第6期)。
对金庸及其小说的文化学思考,也开始得很早。如金庸为什么在写作的巅峰时期毅然搁笔?刘爱华、唐峻山的《走向寂寞:金庸“功成自退”的文化意义的尝试性心理描述》(《艺术广角》1992年第 5期)对此作出了思考。钟晓毅的《拔剑四顾心茫然—— 略论金庸小说中的孤独退隐观》(《广东社会科学》1995 年第1 期),张乐林的《金庸武侠小说的退隐意识》(《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也可一读。而吴晓黎的《90年代文化中的英雄 —— 对金庸小说经典化与流行的考察》(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一文,展示了金庸怎样在90年代逐渐占据文化英雄位置的过程。同类的文章有陈尚荣《90年代文学语境下的金庸》(《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 5期)和《金庸能走多远?—— 关于金庸热的文化汉境透视》(《当代文坛》2002年第 1 期)。金庸小说中所承载的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颇引人注意。卢敦基认为:金庸一方面利用厚重的古代文化思想,用作武侠小说的深刻内涵,《 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与儒、道、释遥遥相对,一方面又利用《侠客行》、《鸳鸯刀》、《鹿鼎记》体现了反文化思想,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浙江学刊》1991年第1期)。何平则从儒学角度解剖金庸,认为金庸自儒入手,以反儒为结束(《侠义英雄的荣与衰》,《读书》1991 年第4期)。胡河清看到:金庸小说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独有的视点,由此可以观察到中国文化范围内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情感形态 (《金庸小说的伦理情感》,《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周宁通过对金庸小说文本研读,指出武侠小说的意义在于华人文化对它的利用(《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对金庸小说中男权思想进行批判的论文有3篇,即丁莉丽的《金庸的悖论:传统男权尺度与现代女性观》(《浙江学刊》1997年第 5 期),芦海英的《情爱世界的阴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 3期)和彭红卫的《男权的狂想与没落——论金庸、古龙小说中的男权意识》(《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相关论文还有:贾耘田的《中国武术文化与金庸小说的武打艺术》(《通俗文学评论》1995年第 2 期),冷成金的《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 期),孔庆东的《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通俗文学评论》1997 年第1 期),方伯荣的《试论金庸精神》(《嘉兴教育学院、嘉兴高专学报》1997年第1 期金庸研究专辑),李咏吟的《金庸小说叙事与民间文化理想》(《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 4期),吴晶的《金庸小说的江南情韵》(《浙江学刊》2000年第 1期),徐岱的《论武侠文化——关于金庸小说的人文思考》(廖可斌编《金庸小说论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龚刚、骆轶航的《金庸小说的文化阐释》(《论文集》),胡小伟的《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第 2期),禹康植的《论金庸武侠小说中“武”的特色》(《华夏文化》2004年第1期)和《论金庸小说中“忠”与“孝”的表现与超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1期),袁杰的《试论金庸小说的叙事结构艺术》(《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1期),龙彼德的《美,在他心目中的中华——论金庸小说的民族特征》(《嘉兴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张群芳《金庸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身份认同》(《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傅如一、魏晓红的《金庸小说的艺术魅力》(《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施爱东的《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杨春燕的《金庸:一个传统文化审美神韵的自觉追求者》(《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廖斌的《无父、审父与弑父:金庸小说人物设置与命运模式解读》(《南平师专学报》2004年第3期),严家炎的《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孔庆东的《论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李存的《论金庸小说的悲情意识》(《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田智祥的《对金庸武侠小说批评的思考》(《荷泽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从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看金庸武侠小说对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金庸武侠小说的现实指涉与理想人格建构》(《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由社会乌托邦的营造看金庸武侠小说的人文关怀》(《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高东洋的《刀光剑影话金庸——对金庸小说争鸣现象的历史考察》(《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吕晓明的《试论金庸武侠小说的审美内涵》(《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王维燕的《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模式的成因》(《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张根柱的《历史文本的传奇化与文学文本的历史化论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写作策略》(《华文文学》2005年第1期),胡小伟的《侠义、正义与现代化——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解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张乐林的《试论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的政治情结》(《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四、金庸和其他作家的比较
最早将金庸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的是文学史家章培恒,他在《书林》1988年第11期发表《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文,引起广泛讨论。 《李自成》一文第二卷曾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代表了当时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而章培恒指出:金庸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均高于《李自成》,前者“假中见真”,人物性格真实而有感染力量,后者“真中见假”,导致读者的幻灭感。这是一次直率的发言,它第一次跨越了金庸小说自身的范围,而大胆介入大陆当代主流文学的领域。此外,章培恒还写了《金庸武侠小说与新思想》(《论文集》)一文。其后的比较多在通俗文学范畴进行,如曹正文的《金庸古龙比较说》(《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相关文章还有张景的《金庸与古龙》(《今古传奇》1992年第 1 期)、张弢的《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中华传奇》1995年第6期)和余杰的《求索真自由——从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看金庸与古龙之自由观》(《论文集》);林文勤的《金庸与张恨水小说之比较》(《通俗文学评论》1998年第4 期)和孔庆东的《张恨水与金庸》(《论文集》,以及陈金泉的《从〈红楼梦〉到张恨水小说:中国小说艺术一条永不竭的长河——兼论张恨水与金庸之比较》(《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首先将金庸和外国作家比较的,是宗源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 4 期的《金庸、勒卡雷异同论》。勒卡雷是一位成功的英国间谍小说作家。而陈墨将金庸放在世界文学范围内考察,显得视野开阔。他把《鹿鼎记》和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世界名著《唐吉诃德》比较后认为,《唐吉可德》是一部杰出的讽刺艺术佳作,《鹿鼎记》则是一部优异的幽默艺术杰作;《唐吉诃德》的诞生,标志着西方骑士文学的终结,骑士的时代迅速地被法律的时代所代替,而中国人对武侠文化的喜好,至少心理上潜藏着古代农业文明的价值积淀;前者追求理想,后者认同现实,两者都是各自作者在各自的时代卓越的艺术创造,而且也是对各自时代最敏感、最深刻的把握。(《〈唐吉诃德〉与〈鹿鼎记〉比较初论》,收入《孤独之侠》)严家炎选取了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小说中对待复仇的态度、艺术风格、小说所体现的各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涵量四个窗口,对金庸和大仲马的作品作了观察,并认为金庸作品在文化内涵上较大仲马为优。(《似与不似之间——金庸和大仲马小说的比较研究》,《论文集》)黎明的《福克纳与金庸小说比较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一文中对福克纳和金庸之间的相同之处作了比较研究,值得一读。
随着“重写文学史”讨论的深入,可以预见将金庸和其他作家特别是新文学作家和古典作家的比较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充分,徐保卫的《金庸小说中的鲁迅维度》(《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 期)一文,已经透露了这一消息。同类论文还有方伯荣的《鲁迅金庸初步比较》(《嘉兴学院学报》2002年第2 期 )。严伟英从浪漫情怀、戏剧结构、叙述角度和视觉运用等四个方面,讨论了金庸小说和《红楼梦》的得失长短,文字优美(《金庸小说与〈红楼梦〉的几点比较》,《论文集》)。相关文章还有徐晋如的《作为反〈红楼梦〉的〈鹿鼎记〉》(《论文集》)。另有施爱东的《从史诗英雄到武林英豪——金庸小说与民间文学关系之一种》(《论文集》)。
五、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自1985 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之后,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把金庸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背景下,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小说史的发展进程,这样的论文如陈洪、孙勇进发表在《南开学报》1999年第 6期的《世纪回首:关于金庸作品经典化及其他》。
1994年10月 25日,金庸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严家炎在金庸受聘典礼上,发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讲话,认为金庸的艺术实践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严家炎的发言还只是一次提示,而王一川则做出了“颠覆教科书”的尝试,他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时,将金庸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而现代文学史上的习惯座次“鲁、郭、茅、巴、老、曹”中的小说家茅盾落选。1998年有 4篇论文探讨了“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这就是钱理群的《金庸的出现引起的文学史思考》,陈墨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通俗文学评论》1998年第 3期;刘再复的《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陈平原的《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 5期。陈墨认为:如何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并研究其意义、价值及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实已涉及对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评析及对这一段文学史学术框架的建构。钱理群认为:金庸小说将现有的文学史叙述结构打乱了,并因此有可能讨论通俗小说的文学史地位,进而重新认识与结构20世纪文学史的历史叙述;这种讨论并无意于在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及其经典作家鲁迅与金庸之间作出价值判断,而是要强调二者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有着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特点。新文学的现代化的推动力是双向的,既包含了文学市场的需求,也有思想启蒙的历史要求;而通俗小说则是在文学市场的驱动下,不断进行现代化的变革尝试。刘再复试图摆脱以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的偏见,在新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学传统两条线索分流演变的认识下,重新检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并以此背景理解金庸对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确认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金庸以自己杰出的文学才华成为与新文学传统相对的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使本土文学再次发扬光大;在政治权威侵蚀独立人格、意识形态教条干预写作自由的年代,金庸的写作就是文学自由精神的希望;他对现代白话文和武侠小说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王海林,罗立群,曹正文三人的三种武侠小说史都高度评价了金庸小说,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怎样给金庸以恰如其分的定位呢?我读到的10余种相关文学史,只有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用一小节介绍了“金庸等人的通俗文学创作”;以及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九卷(华艺出版社1997版)有一小节涉及“梁羽生,金庸及各种流行小说”,其他的或避而不谈或坚持以往的叙述传统。
六、关于金庸小说的论争
20世纪80年代,金庸小说在民间流传的时候,文化界的主体态度是冷漠和沉默。至90 年代,关于金庸小说的大规模论争有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 1994年,导火线是王一川将金庸选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和金庸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时间持续至 1996年。论争中态度最生硬的是鄢烈山在 1994年 12月2 日《南方周末》发表的《拒绝金庸》,表示自己从不看金庸小说,因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相关的讨伐文章还有骆爽的《金庸武侠神话的终结》(《为您服务报》1995 年 9月21 日) , 和王彬彬的《“红学”、“金学”》(《 中华读书报》1996年 1月 3日)。上述短文立论粗暴,情绪激烈,令人费解。相反一些平心静气的讨论,却能启发人思考,包括陈辽的《且谈“文学大师”》(《文艺报》1994年 10月 22 日), 和李庆西的《作家的排座次》(《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 12月 10日)。林焕平在《关于文坛重排座次的问题》一文中反驳如下观点:1,金庸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说;2, 金庸小说是“静悄悄地进行着的一场文学革命”说;3,金庸是“继《红楼梦》后第一人”说;4,金庸小说是“空前绝后”的文学说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 年第3期)。文章条分缕析,言之有据,非常耐读。相关论文还有司马奇发表在《作品与争鸣》1996年第 2期的《关于文坛 “重排座次”的讨论和思考》。
第二次起因是 1999年11月 1 日,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发难,用《我看金庸》攻击金庸小说等四大俗,而王朔自己开始以主流文化的发言人自居。金庸在 11月5日的《文汇报》以《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迅速作出回应,随后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一场激烈论战。评论界关于这场论争的初期情况,巫勇的《东风西风劲吹声——王朔金庸论争综述》(《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 4期), 一文可以参考。随着讨论的深入,话题的延伸,出现了不少论证严密的学术文章。王彬彬除了在 1999年 11月 18 日《羊城晚报》上有《金庸给他们带来什么》一文参战外,还在2000年第 6期《红岩》发表长文《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葛红兵在 2000年第 1 期的《探索与争鸣》,则有结论相近的《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论金庸与王朔之争》一文。曾庆瑞、赵遐秋在《金庸小说真的是“另一场文学革命”吗?——与严家炎先生商榷》一文中,坚持认为金庸小说代表旧文化,并批评以反封建为标记的“北大的校格”已经蜕化(《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 4期)。而吕周聚的《金庸不等于贵族文学》(《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 2期) 是反驳葛红兵的文章;徐岱《批评的理念与姿态——也以金庸写作为例》(《文艺争鸣》2000年第2期 ),是和袁良骏《再说雅俗—— 以金庸为例》(《中华读书报》1999年11 月10 日)一文商榷。浙江大学出版社在2000 年 11月出版了廖可斌编的《金庸小说论争集》,“编者的话”指出:“为尊重对方的观点而放弃或掩饰自己的观点,是平庸和虚伪,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剥夺别人发言的机会是自私和褊狭。坦率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尊重不同意见,不自欺欺人,不自侮侮人,是编者追求的境界。”这一说法可谓意味深长。
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一全新的媒介,这次论争的范围和规模远远超过1994年的那场争论,被称作“网上文坛第一争”(雨辰《看王朔骂金庸引发的网上论争》,《人民邮电》1999 年 12 月 12 日)。出版社的反应也是迅速的,很快有两本书问世,即张峰编的《王朔挑战金庸》(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和文硕、李克编的《我是网虫我怕谁:网民对垒“金王论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版)。关于网络金庸的初步探讨,有龚鹏程的《e时代的金庸——金庸小说在网络和电子游戏上的表现》(《论文集》);相关资讯见葛涛《互联网上的金庸》(《网络金庸》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版)。
对金庸小说艺术缺陷的批评也一直不绝如缕,如朱国华的《关于金庸研究的一点思考》(《文艺评论》1997年第 3期),阎大卫的《班门弄斧——给金庸小说挑点毛病》(海天出版社 1998年版),王际兵的《在现状下的迷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 年第 3 期),徐皓峰的《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恶俗”因素》(《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 5期),等等。敬文东的《流氓世界的诞生:重读金庸》(花城出版社 2003年版) 语带抑揄,而陈东林的《人妖的艺术——— 金庸小说批判》(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则近于辱骂。
七 作为一门学科的金庸研究——“金学”
“金学”之说,出于港台。最早提供相关信息的是章巽在 1988年 4 月 30日《文艺报》发表的《台港“金学”一瞥》,其后有古远清的述评《台湾的“金学”研究》(《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1 期) 和《香港的“金学”研究》(《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 1期)。丁进在《“金学”的四个相关学科》一文中谈到:金庸研究的相关学科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新武侠小说、通俗文学和红学 (《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 1 期);他在《金庸小说研究史略》一文中,第一次描述了金庸研究的发展过程(《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 4期);此外,他还编有《中国大陆金庸研究目录(1985~1999)》,刊于《文教资料》2000年第6期。
陈墨的《“金学”引论》一文,从雅俗之辨、名实之辨、冷热之辨三方面谈到“金学”的学科建设 (《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第 3 期)。朱寿桐也写有《谈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嘉兴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期)一文。赵汀阳的《能成“学”的文学作品》,用不长的篇幅揭示出一个规律:要构成“学”,就必须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而且可以不断扩展谈论范围,以至形成一个路路相通、层层相关的“话语网”。这种“学”虽然可以有学术的成份,但其主要性质是一个广义的文化交流场所,并不是非常专业的学术。像莎士比亚的戏剧, 《红楼梦》和金庸的武侠系列就可能成为“学”(《博览群书》1996年第 9 期)。王一川《文化虚根时代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一文则认为:金庸为处于现代文化虚根危机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认同模式,金庸小说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价值系统的现代性风貌,为现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价值建构确立了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想范型(《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 5 期)。
作家研究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应该和可以成为一门学科。纵观 20世纪中国学术史,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作家研究实在很少。而像金庸这样的优秀作家的研究,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金庸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繁荣通俗文学创作,框架20世纪中国文学史,而且还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建构21世纪的文化形态。
八 大陆金庸研究的不足与瞻望
近几年来大陆的金庸研究确实出现良好的征兆,也发生某些内在而深刻的“质变”。诸如人们的文学观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金庸被排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列,并从大众读者中走上神圣的学术讲坛。1999年3月,金庸还被浙江大学文学院聘为院长。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仍存有很多的问题。虽然金庸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名榜上名列第四,虽然把金庸研究与《红楼梦》研究相提并论,称之为“金学”,可当代出版的那么多文学史,为什么不把他写进去,难道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陈旧观念依然是那么根深蒂固吗?虽然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已把金庸纳入文学史叙事之中,这是一种尝试,但如何公正合理地确立金庸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似乎没得到真正解决。显然,这是与金庸小说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蕴及他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巨大贡献很不相称的。为了使金庸研究出现新的发展,使之可与鲁迅,沈从文,巴金,老舍等作家的研究比肩,除了发展壮大研究队伍,除了资料的挖掘,拓展外,还应该:首先,拓展深化金庸的研究领域。金庸是个多面手,他是集学者,编剧,导演,老报人于一身的作家。他精通法律,佛学,民俗学,四裔学,历史,地理,谙熟外国文学,电影,音乐,舞蹈,棋艺,交游甚广,懂得多种语言。因此,所谓金学研究不仅应包括他的武侠小说,还应包括其它领域。我们的学者大多关注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对他的其它贡献则涉足很少,几乎为空白。近年来陈平原试图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他从金庸《左手写政论,右手写小说》这一角度切入,探讨金庸超越雅俗的成功之因及今后武侠小说的出路问题。大陆金庸著作的出版现时十分混乱,许多盗印版质量相当粗劣,大多数学者依据的文本是经金庸修改过的版本(1970年——1980年约10年修订完成),而我们现在的读者看到的也大多是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36集《金庸作品集》,这也是金庸的修订本。究竟修订本与原版本有何优劣?金庸为什么要作如此大幅度而认真的修改?大陆学者在这一点上似乎还缺乏深入探讨。其次,更新金庸研究的理论方法。独特的理论方法不仅意味着角度的新颖,而且代表着观念的变更。前文提到陈墨,陈平原等将叙事学的理论及方法引入金学研究,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我们倡导把更多的新方法运用到金学研究之中,包括精神分析,人类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民俗学,阐释学,接受美学,原型批评,比较研究等等,都是切合金庸这个具体研究客体的。我们期待更多高质量的具有理论深度的金学研究论文的出现。最后,加强对负面效应的研究。我们在肯定金庸小说的重要成就及贡献时,也应该看到金庸武侠小说给读者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我们的大部分学者则一反新文学作者的激烈批判态度,大肆褒扬金庸小说,这也是不够客观的。我们在考察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时,不能抹煞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也不能否定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但真正的学者应该科学地客观地评价金庸小说的价值及其意义,这应该成为未来金学研究发展的一个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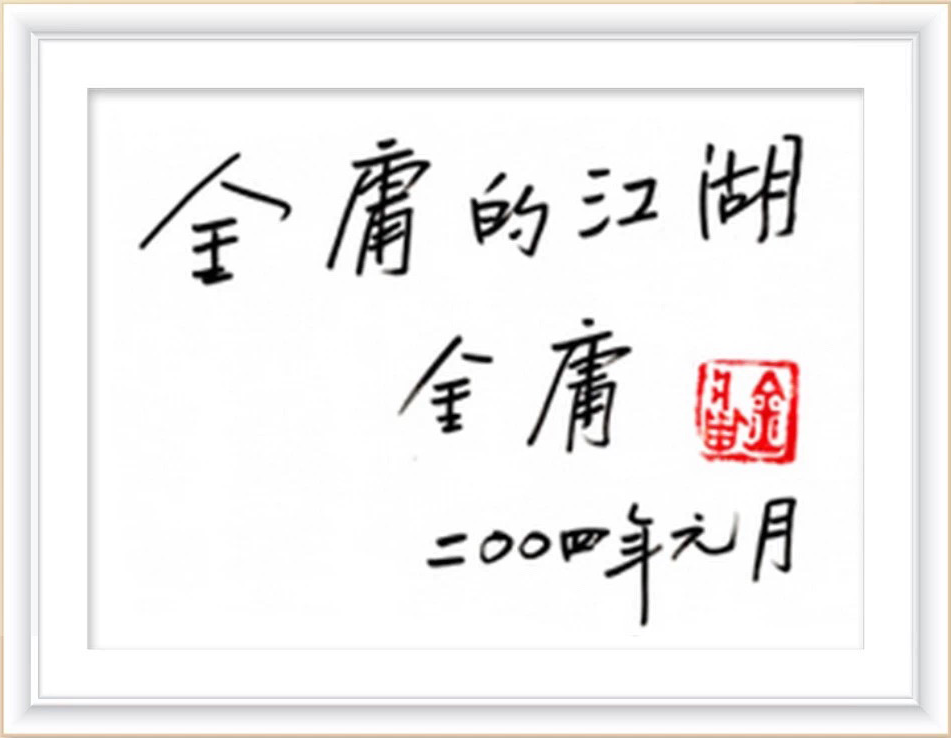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