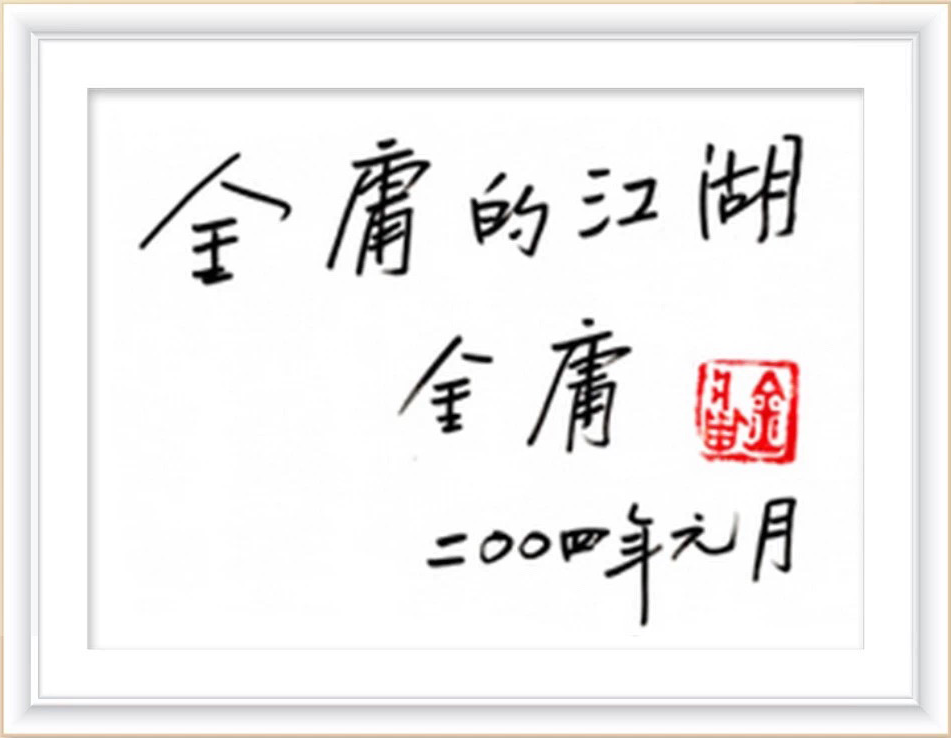作者余兆文,系金庸高中同学
一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浙江杭、嘉、湖地区相继沦陷。1938年夏,我和金庸都流亡到丽水碧湖浙江省立联合中学去读书。我们两个恰巧被编在初三年级同一个班。
初中毕业后,我到衢州中学去读高中,金庸就近考入联合中学高中部。但他在该校高中部只读了一年,1940年夏就因写了一篇诙谐的文章,触怒了训育主任而被学校开除了。
那个暑假,我正在金华住院医病,金庸匆匆从碧湖赶到金华来找我。他希望转到衢州中学去续学。我那时其实是把气管炎误认为肺结核,并无大病,要走就走,于是我们随即收拾了一下,便一同乘火车来到衢州。
在衢州城里吃了中饭,我们两人倾囊倒䇲总共只剩下八块多钱。可他却一时心血来潮,撺掇要到文具店花六块多钱买一副围棋,我言听计从,买就买吧。明天不吃饭啦?明天的事何必今天操心!
我们步行来到离城十多里一个叫静岩的小村子,这是抗战时期衢州中学的临时所在地。
不错,“车到山前必有路”。在静岩,我们食宿不但没有困难,生活享受还相当高级,简直可说是养尊处优呢。很幸运,我们居然能在那家平时专包教师伙食而暑期生意清淡的餐馆里包了伙,又租赁了村头一所颇有田园风味的小房子。因为我们囊空如洗,饭钱、房租无现款可付,都是赊账挂欠的。
我们可谓称心如意地在静岩暂且安顿下来了。金庸此行是专程来衢州中学转学的,当务之急,本该立即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应付日内的插班考试。但他梦魂萦绕的却是围棋。大概他在高一读书时学会了围棋,现在没有弈棋对手,玩不起来,棋瘾难熬,无奈只能临时教个徒弟,拿自己现教的徒弟凑合过把瘾。
他从早到晚谆淳教导,要我记住:“金角、银边、草肚皮。”强调首先要抢占棋盘四个角,因为角落最容易存活:其次是争夺边缘;而后再转战中央,在棋盘腹部攻城略地。
他煞费苦心、不厌其烦硬把围棋基础知识灌输进我的木瓜脑袋。
有时,他一边教棋,一边说些棋坛轶事:说围棋名人福建人吴清源九岁时,就被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特邀到北京家中弈棋,段祺瑞还是他手下败将;又说吴清源成长后让人四个子,谁能与他对弈交手,有力招架,其棋艺仍居一流,还不失为国手。
他还说,吴清源后来东渡去日本,一直以围棋为业,因为那时我国棋坛不温不火,而在日本,围棋却是风摩全国,由于有实业界的资助,棋赛奖赏丰厚;棋书棋刊种类繁多,有似雨后春笋;围棋开赛之日,举国若狂,热闹非凡;吴清源后来在日本棋坛被公认对围棋极有影响的人物。
他又说:日本有一位围棋高手,有一次围棋一开局,便将第一颗子扑笃一下投落在棋盘中央,观众大为惊奇,此举后来都被棋坛传为美谈佳话。金庸曾几次喜滋滋对我提及此事,好像他对这位日本棋手的标新立异、敢于犯忌,也颇为赞赏。
二
金庸带我在围棋天地厮混了半个多月,衢州中学插班考试终于到期了。他毫不费事考取了高二插班公费生。他这次衢州之行,可说收获丰硕,转学已经顺利转成,还顺便带出了一个围棋徒弟,虽然不能说名师出高徒,但以后总可以随时马马虎虎过把瘾了。
为了办理转学手续和搬取行李,金庸就赶在开学以前到碧湖联合中学去跑一趟。碧湖离静岩不远,约四百里,单程一般仅是从容不迫一天的路途,但他在碧湖很可能是被围棋老对手缠住,人不留客,棋留客,过了六七天,他才迟迟回到静岩。随身带来了三件行李:一卷铺盖、一只箱子和一个网篮。那个网篮里全是盒盒罐罐吃的东西,有饼干、糖果、月饼等糕点,还有不少罐温州炼乳。
这三件行李使他一路劳累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他在宿舍日以继夜睡了两天,仍然末能完全恢复疲劳。
我怜惜叹道:“路上何必自讨苦吃,硬要带上这一网篮劳什子吃食,多个拖累?糕点零嘴可以在这里买嘛!碧湖的东西并不比这里便宜。”
他说:“这些都是慰问品啦!有些老同学听说你生病,一定要送点东西慰问一下。”
这又令人绕头了。金庸这次回联合中学转了一转,在碧湖老同学的印象里,我的一点气管炎好象突然变成沉疴经年,百药无效,只靠糕点零食了。当然,这一篮子零食的来路与金庸的非凡才华和真挚友谊在同学心目中的地位不无关系,他的棋艺恐怕也起了点作用,单凭我的名义即使费上很多口舌去化缘募捐也难搞到手的。
金庸转学到衢州中学以后,更是有教无类不遗余力又带出了一批围棋徒弟,很多同学的课外活动重点慢慢由篮球转移到围棋。每天下午课后,宿舍逐渐成为业余棋院,徒弟与徒弟,徒弟与师傅常为让一步棋或争一只棋,不但相互斗嘴讥讽,有时还动手抢子,叫叫嚷嚷,笑闹不已。但一直闹到高中毕业,芸芸众徒之中还没出现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新秀,金庸这个衢州中学围棋的开山始祖,仍是该校的第一顶尖棋手。
金庸后来进入新闻界工作,是不是还下围棋呢?1981年他从香港回到阔别久违近三十年的家乡,我很想知道他早年对围棋的爱好有无改变。
我试问:“你几十年来一直当记者,要东奔西跑,采访新闻,什么地方都去过,忙吧?”
他道:“除了南美洲,世界上一般国家都去过了。你到过什么地方?”
“我呀,我从前扛得动锄头时,常常到农村去,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是大有作为的。”我随口回答了两句,仍旧追问:“那你离开大陆后,早年周游列国,马不停蹄;后来在香港一边忙于创办《明报》,同时又赶写小说,恐怕多年没下围棋了吧?”
他却正正经经而不无自豪地答道:“我现在是围棋业余六段。”
天呀!真是难以置信。他在百忙中对围棋还如此锲而不舍,乐此不疲,而且棋艺突飞猛进,青云直上了。六段已是业余围棋的最高段位。
八十年代初期,那个一连扳倒日本五、六位围棋高手而最终获胜的聂卫平鼎盛时期,有一次因赛事去香港,金庸曾特地恭请聂卫平到他家中,亲身当面领教过聂卫平九段的高超棋艺。他这个荣誉业余六段的港报巨头居然和当时头戴围棋桂冠的一代棋圣碰上了头,他和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也曾触膝对弈,交流过棋艺。
金庸也很关心国内围棋比赛。1985年跟着《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的广泛放映,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在全国十分畅销,第二年他来南京旅游访友,我探问:“你这两年的版税很可观吗?”
他含笑道:“国内出版社跟我洽谈协议的是不少,估计销售几千万本。但只有天津一家出版社付了三万块钱,我已捐给当时在安庆举行的全国围棋比赛了。”
三
如果金庸可称得上棋迷,那他更是个实实在在嗜书如命的铁杆书迷。
在碧湖读书时,由于联合中学是杭嘉湖地区几个公办中学临时拼凑起来的,学校的一些设备只能因陋就简,有些甚至残缺不全。阅报室是开辟了一个,图书室就一时筹建不起来了。
平日金庸只能到阅报室去看看报,要看课外图书呢,那只能在节假日去光顾碧湖镇上那家独一无二的小书店。
说实话,我跟他去逛书店,无异陪公子读书,有时听他说几句书评或读后感。我每天能完成老师布置的那点作业,就已勉为其难,聊以自慰了,还会看别的什么与考试无关的课外读物!
金庸每次走进书店,便挑选一本喜爱的书,立刻倚靠在书架旁边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或细看,或略读。有一次,他翻阅了英国威尔斯《未来世界》的中译本,离开书店时,他对我说:“未来的世界大战,不再有近战、肉搏战,打仗时只要坐在实验室里看看图表、按按电钮。”
有一天,在书店里,他津津有味看过了沈从文的《边城》,禁不住赞道:“这本小说,人物很少,情节简单,篇幅也不长,但很有诗情画意。”
每次我们逛书店,一般都是他阅读书刊,我翻看画报。有一次,我从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他从旁边望了一眼,说道:“这本《莫里哀戏剧集》是王了一翻译的,只有上册,没有译完,下册还没出版。”
我听他说这话,一时莫明其妙,这里有成千上万本书,怪哉!我只知道徐志摩是他的亲戚,难道这个王了一又是他的什么熟人?
金庸时常带我光临书店,书店老板是没有多少好处的,我们只会把他的图书搞脏弄旧,我们口袋里即使难得有几个钱,那也只能照顾自己一张馋嘴,留着买几个街上比比皆是、油煎的香喷喷的罗卜丝馅饼。不过我们常去书店逛逛,也让那家书店显得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无意中给书店做了义务活动广告。
他转学到衢州中学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衢州中学是有图书馆的。衢州中学只是为了躲避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方才从城里暂且搬迁到乡下,学校的图书并无什么失落。因此金庸在衢州中学就不必上街,硬要把人家的书店当图书馆,厚着脸皮两腿酸痛站在书店里看书了。
学校图书馆开设在一个离静岩高中部两里路光景的小寺庙内。因为那里地方狭小,图书馆没有开辟阅览室,只是专门经管借书工作。金庸是光顾图书馆频繁的常客,三日一叠,五日一包,课余之暇,手不释卷,午睡时也不休息。有一天,班主任老师不由得开口训道:
“看起书来,命都不要了。不顾健康,这样下去,你会后悔莫及的。”
中小学生因为逃学懒学而被老师责骂是常有的;但由于好学勤学而被训斥的实属罕见。
再说,衢州中学和联合中学很不一样,外地流亡来衢的学生很少,绝大多数学生是本地人,所以在衢州,我们常常被邀请到同学家里去作客。金庸访友作客总是改不了他那独有的积重难返的老习惯。他每次一走进大门,便立刻在这个人家的书架、书桌等放书的地方踅来踅去,一双手忙着在书堆里抽抽插插倒腾起来。主人把瓜果茶点端出来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专心致志翻阅他最关心的本本册册,一直要等到把这里的书架书橱统统搜索了一遍,他才老老实实安心走到桌边坐下来。
这时,倘使有人问他这个屋里有些什么书,他准能把这里所有的,不论新书还是古籍,正确无误如数家珍地随口说出。当然这些并不是他自己的家珍。
而在这次作客期间,这些书便是他无可代替的精神食粮。如果这个东道人家委实没有什么新书可读。那他只能等而下之,将就把那些几乎家家都有而他却早已读熟的《三国》《水游》、《红楼梦》之类再翻看一遍,又炒一次冷饭,似乎也不嫌腻。
金庸很喜欢看林语堂的幽默文章;茅盾、曹禺、老舍的著作他也颇有兴趣;他对鲁迅打算撰写以章太炎为首代的三代知识分子为内容的长篇小说《三世同堂》,因天不假年而未能写成,甚感惋惜。
我问他究竟最喜欢看什么书,他毫不迟疑答道:“是武侠小说。”他似笑非笑说道,他看过的武侠小说可能比大学教授也不会少。
四
高中毕业后,金庸离开了衢州,经历长途跋涉,奔赴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陪都重庆,考进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他上大学读书,与其说他“求学",不如称其“自学”。图书馆阅览室似乎比上课的教室对他更为重要。因为图书馆里有很多各种各样书籍和刊物,他平时一有空闲,便去自得其乐泡图书馆。
那时,内地大概由于运输不便,纸头紧张,大学里缺少课本,尤其是文史哲政法等一类人文方面的学科,一般大学老师大都自编一份教材,上课时昂然拿到教室里去对着学生照本宣读,老师读一句,学生记一句。老师读完一课时打烊,学生闭上笔记本收摊。
金庸上这一类课,从来不记什么笔记,他连笔记本都没有。在课堂上他只是袖手聆听。可是竖起耳朵全神贯注的。
临近考试,一般学生死记硬背自己那点平日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宝贝笔记。金庸无笔记可背,但他早在上课时,当堂已把老师宣读的那点东西牢记在心,宛如今日把老师那点教材输入了电脑。更可贵的是他会到图书馆去认真阅读老师推荐的有关参考书。参考书当然远比别人那点笔记详细全面,因此,他这个不记笔记的学生,考试成绩常常是全班最好的头名状元。
学习法文课是有课本的。有课本,他也要看点参考书。为了研究古希腊女诗人苏福,他曾要我向别的学校代借法文有关参考书。
历史课刚刚学过、考过。但考过之后,在暑假里,他自己又认真阅读英语原版的威尔斯《世界史纲》,这本书他是随身携带英文字典,见生字必查,逐字逐句细看精读的。这也让他既丰富了历史知识,又增强了研读英语能力。
总之,他在大学学习文史政法等学科总是不满足于课本和课堂知识,他难以离开图书馆阅览室。
中央政治学校是一所国民党党校,与一般大学不尽相同,时常邀请一些普通学校不容易请到的达官显宦、御用学者去讲演。金庸对这些显贵所讲的内容好象多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足挂齿,而对他们的生活小事,有时却颇感兴趣。
他说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去中央政治学校讲演,每讲一会儿,就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放在嘴里嚼嚼;讲了半个小时,又随便拿出一个睡帽怪模怪样歪戴在头上;讲完以后,离开礼堂,刚走出学校大门,在上小车以前,这位部长老爷居然会在前呼后拥、众目暌睽之下,顺手解开裤子,站在路边随地小便。孔祥熙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是个显赫一时的人物,谁知竟是这样一个活宝
五
1944年秋,金庸还在大学二年级读书,却因拒绝学校号召报名参军而被中央政治学校无理开除。但是,吉人天相,经过熟人介绍,他有幸进入当时藏书最多的中央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分配他管理阅览室。这是个实际上有职无事的差使,正好让他在这个浩瀚书海中心安理得读他喜爱的书,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在别人眼里,他平时博览群书,好象是随便拿到什么书,都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平?”其实,他读书,有时是有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四书》《五经》他幼年时已经读过。一部《庄子》更是滚瓜烂熟。这时他开始较为系统全面地阅读《史记》《资治通鉴》等经典著作。
同时,他又大量阅读英文版的世界文艺名著。他一度好象曾把《大英百科全书》里文艺书的排名作为读书指南。闲谈时,他说:“世界最佳十篇短篇小说是《项链》(法)、《赌博》(俄)、《美人乎?猛虎乎?》(美)等;世界最佳五十部长篇小说是《大卫·考佩菲尔德》(英)《波华利夫人》(法)、《战争与和平》(俄)等等。他是重视大作家的巨著的,但也不忽视小作家的名作佳篇。
他对英美诗歌也很欣赏,曾经念读过英国青年诗人拜伦、雪莱等人的英语原文诗篇。不知何故,他对美国那位擅长描绘人的异常心理的爱伦波饶有兴趣,还翻译过他的短篇小说
别人敬而远之的文字玩意,金庸有时也会提笔尝试,他曾大胆将《诗经》译成英文。我后来和一位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学的朋友谈起此事,这位朋友苦笑道:“哈哈,即使要我把这种古文古义的‘关关雎鸠’译成现代白话文诗歌,我也只能拱手辞谢:‘饶饶我吧!’”
倘若说金庸孜孜不倦读书是刻苦学习,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恰当。他看书根本就不辛苦,正好相反,却是莫大的乐趣。
我有时对他说:“我情绪不好,心里烦闷时,什么书都看不进。”
他却说:他一看起书来,什么烦恼苦恼都忘掉了。
如果说他看书“一目十行”,那是个相当合适的赞誉之词:要说他读有些文史书籍“过目不忘”,若不是求全责备,他也可当之无愧。
一木美国作家霍桑的《红字》,本文虽不太长,可序言不短,全书总有二三百页吧。有一天,我们上街去泡茶馆,他一边喝茶、嗑瓜子,一边翻阅那本《红字》,居然会在两小时以内一口气看完,并叹道:
“这本小说相当阴沉悲凉。”
一部法国大仲马《基度山伯爵恩仇记》的英文译本,上下厚厚两册。大仲马著作里的人物多有侠义之气,金庸拿到了这部小说,如获至宝。晚饭后,他连忙回到宿含,立刻坐进被窝,背靠墙,手拿书,爱不忍释阅读起来,越读越有劲,一直读到深夜,书读完了,情犹未了,深深沉迷在书中。这部书对他的思想情感似乎有点影响,而他后来的个人经历和基度山伯爵好象还不无相似之处。
六
金庸在青年时期虽然称不上影迷,可他对电影的兴趣还是很浓厚的。他的电影知识也十分丰富。1943年夏末秋初,我们在重庆,在大学尚未报到入学的那段时间,每逢电影院放映名片,他一定邀我同去观看,那时放映的多是美国影片。
我们去看过秀兰邓波儿的《绿野仙踪》,也观看过狄安娜窦萍的《小鸟依人》和英格里·褒曼的《爱德华大夫》等等。这些都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大明星的名片,也可说是风靡全球的。
第一次看电影时,金庸赞叹道:“电影院里有不少人的英语水平很不错嘛。”
我问:“你怎样知道?”
他说:“你不听听,电影里的对话不时引起不少人阵阵笑声?”
他这句话才使我冥顽不灵的脑袋开了窍。因为那时的美国影片都是英语原版,没有现在逐字逐句的汉语翻译片。放映英语版片时,只是在银幕旁边加上一点简单的中文解释字幕。我看原版彩片,完全依赖那点中文字幕的帮助。我和金庸当时同是高中毕业,我的英语为什么这样蹩脚,根本不可和他同日而语。
有些有识之士断言:“一个人要事业有成,需要一分天才、九分努力。”但金庸的语言文学天才决不只一分二分,他又是十分努力,还加上十二分爱好呢!因此,有人把他和那个解放前为人熟识,当过国民党行政院长的王云五相比,等量齐观,那是瞎子摸象,乱比胡扯。
王云五原来只是个上海滩以兜售书报糊口的小摊贩,后来虽然赫然发迹,成为中国最大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老板,似可与金庸凭一支笔杆创办香港《明报》集团公司互为伯仲,不分轩轾;王云五又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访英代表团团长,他的英语呱呱叫,也是自学成材的。但金庸1992年被举世闻名的英国牛津大学聘为访问院士,并在牛津这个高等学府用标准英语讲了半年学。何况王云五更没有象金庸那样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撰有《金庸全集》几十部,武侠小说只是其中的十五部,这更是王云五望尘莫及的。
七
再说,有一天,金庸为了看电影,又兴冲冲跑来邀我:“快去,我们去看卡通片《白雪公主》”
我笑道:“咦!卡通片是给小孩子看的,有什么意思?”
他道:“《白雪公主》非同一般,不可小看,是美国卡通大王华特·迪斯尼的名片,得过大奖的。”
后来,我们看过了《白雪公主》。确实非常满意。这部卡通片想象力丰富,画艺精湛,片中的小公主及为其忠诚效劳的小动物都演得活泼有趣,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无可非议是一部出类拔萃、老少皆喜的影片。跟着金痛看戏,没错。
最使我永世难忘的还是观看美国武侠明星埃洛尔弗林主演的《罗宾汉》。这部影片在重庆开始放映,金庸便津津乐道对我宣扬古时罗宾汉其人其事,说罗宾汉在英美等国民间,很像《水浒》中的武松在中国一样,自古至今,一直是妇孺皆知的侠义之士、绿林豪杰。我们两个十万火急赶到电影院一看,不胜惊愕,那天电影院的情景和往常完全不同,售票窗口前面不是平日秩序井然的买票队伍,而是乱糟糟、黑压压一大片人,推推挤挤,人声鼎沸,好像正在抢从天上掉落的馅饼。看看这个架势,今天要搞两张电影票,决不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了。
说实话,我出生在浙西重峦叠嶂一个山窝窝里,野性未改,更善于爬墙攀窗,在人群中钻挤。但他这个书香子弟却当仁不让,毅然请缨,奋不顾身钻入人群,缓缓向前移动,一步步逼近售票窗口。不到半个时辰,他竟安然冲出重围,一手捏着电影票,一手护着眼镜,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显得筋疲力尽,元气大伤。但一个文弱书生能如此奋勇拼博,志在必得,不亦可歌可泣?无怪乎他后来赫然成为中外扬名的金大侠。果然不出所料,《罗宾汉》确是我平生看过的最佳影片之一,导演设计十分奇妙;剧情变幻惊险,扣人心弦;尤其是饰演罗宾汉的埃洛尔弗林气宇轩昂,英俊威武。他隐匿路边树上,飞劫骑马税吏;攀绳直上屋顶,突袭豪强城堡,其演技无与伦比。金庸认为此片非看不可,是理所当然的,为了一饱眼福,费点力气,流点汗,值得!
可令人费解的是,金庸丰富的电影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他出生在浙江海宁远离县城的由曾祖创建的“赫山房”。这个当地闻名的“赫山房”,其规模大概比《水浒》里扈家庄、祝家庄小一点,可能和“九绞龙”史进的庄园差不多(据说现在当地政府正拟拨款修缮这个金庸旧居),是孤零零坐落在一片辽阔的田野上。他小学是在附近一个乡镇上读的,后来考进嘉兴中学,嘉兴也只是个小城市,当时决不会有电影院。照理,他和《白雪公主》《罗宾汉》之类是沾不上边的。那么,难道就是因为他是个书谜——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最后,我又禁不住还要唠叨几句闲话。
有人说捧金庸是睁眼瞎。我现在实话实说写了这点金庸琐事,算不算捧?我睁眼瞎是无可讳言的。我平生读书很少,孤陋寡闻,近乎文盲,文盲就是睁眼瞎。但邓小平1981年7月18日单独会见金庸,曾当面称赞金庸的《明报》有其独特见解。小平同志现已作古,不然的话,小平同志虽然不会被包括在被骂眼瞎之列,可他脸上也可能会被溅上几点唾沫。这样一想,我更不在乎什么睁眼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