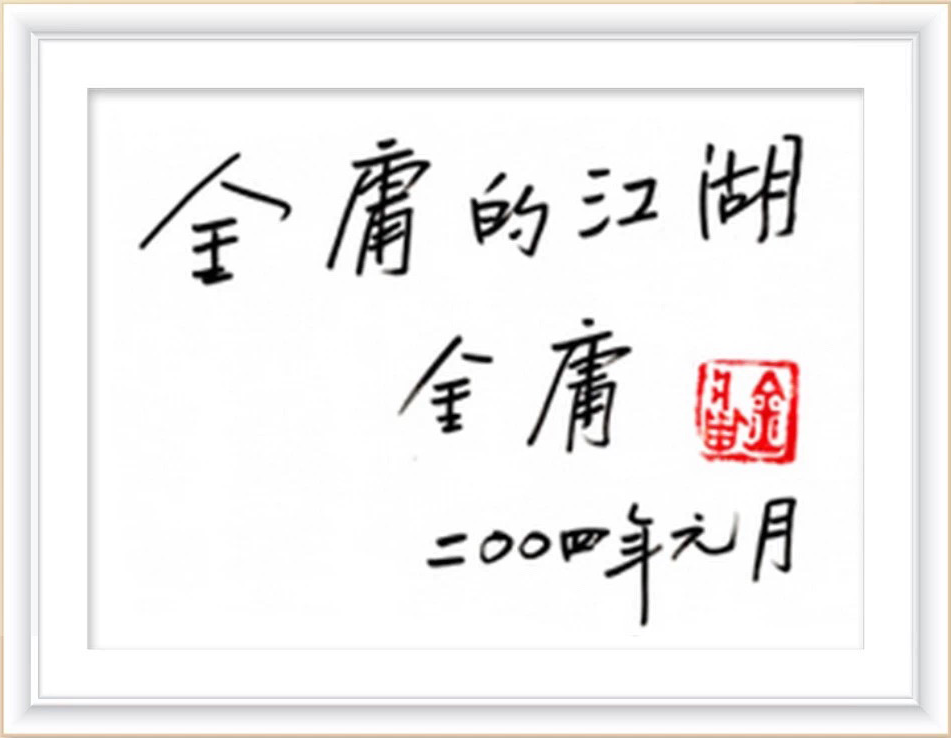作者余兆文,系金庸高中同学
一
凡是读过金庸小说的读者,和看过由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的观众,皆知金庸其名。金庸的原名叫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他并不是个专写武侠小说的文人,更不会耍拳弄棒,而是道道地地学生出身,很早就当记者,今日在香港是妇孺皆知的创办《明报》的名人。
金庸从小喜欢看书,也爱看武侠小说,但他爱而不迷。在小学里,他的文章就写得很
好,在班上非常突出。
读初中时,一位语文教师看了他的作文,竟毫不掩饰地在学生面前流露出一副望尘莫及的样子,喟然叹道:“说实话,要我再读二十年书,恐怕还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转入浙江省立联合中学。读高一时,同学们要他为墙报写篇文章,他就仿效《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描述了学校里的一些奇人怪事,自然也提到那个身负护卫学风校纪之责的训育主任。可中国是个几千年来一贯维护“天地君亲师”教规,而又最会利用各种名义大兴文字狱的国家,那位训育主任又无端失去了封建官爷们“好官我自为之,笑骂由你笑骂”的古风和雅量,今见自己管教下这个乳臭小子,竟敢如此批逆鳞、捋虎须,亵渎师尊,只恨学校没有火刑柱。学校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于是金庸因“亵渎师长,败坏学风”之罪被革出校门,逐出了联合中学。
因我在联合中学初中毕业后,是在衢州中学升高中的,这时,他也愿意转到衡州中学插班。从此,我们又再同窗共读了。
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初夏的一天,有位跟金庸非常亲近的同学,为了一点小事,和一位老师争吵起来。那位老师三十多岁,自认自己身大力不亏,盛气凌人,一边恶狠狠地谩骂那位学生,一边走向前去想动手动脚,还口口声声扬言要开除他。那位学生被逼得忍无可忍,心一横,豁了出去。毅然拾得一块砖头,声言:“如果这样无理开除我的学籍,那我就宁可杀头,也先要开除你的生命籍。”幸亏这时走来几位同学,尽力从中斡旋,又劝又拉,这才避免了一场鏖战。
金庸对于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师道尊严,记忆犹新。今见此事,自然义愤填膺:学生不许批评老师,老师却可以污辱学生,动辄就要开除学生的学籍,这种歪理邪道,他再也不能容忍。他奋笔疾书,写了篇《一事能狂便少年》寄到了《东南日报》。
二
《东南日报》是沪杭沦陷前夕由杭州迁往金华的,这家是当时我国东南地区最大的报纸,居然将金庸这篇文章登在文艺栏最显著的部位。文章没有指名道姓,也不曾就事论事,而只是借题发挥,明辨是非,伸张正义;并且强调干大事、成大器者必须具有大无畏精神,敢于蔑视一切虚假的尊严和顽固的传统势力。他还高度赞扬了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俊杰玛志尼的宏伟气魄。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衢州中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都明白:作者所说的是什么事,指的是什么人。同学们人人争看,无不拍手称快。由于以金庸为首的一些同学的声援,或许也怕那位“少年”万一真的“疯狂”起来,当初那位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老师,竟也渐渐变得识时务了,不再叫叫嚷嚷要公开开除谁了。
《一事能狂便少年》的发表,可说是一文惊人,不久《东南日报》有位名叫陈向平的老资格记者,因事从报馆所在地金华出差到衢州去,这位陈先生在那段时间,他的思绪似乎一直难以保持宁静。他始终觉得《一事能狂便少年》的作者虽然名不见经传,鲜为人知,但他那短短千余字的杂文,论述精辟,笔力浑厚,既有唐宋散文笔调,又具西方文艺韵味,出手颇为不凡,陈向平先生一再思忖:“自己远道来衢,何不趁便登门造访,亲谒其人。查理(当时的笔名)先生究竟何许人也,今日流落至此?”
他整了整衣冠,走到外面打听了一下。讵料衢州中学那时并不像他想当然的就在这个衢州城里。为了免遭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全校师生早已搬到乡下去了,现在一个离城十多里的小村子里。但这位陈先生访贤若渴,毅然不顾十余里之遥,独步趋访。出了南门,踏上了乡间纵横交错的荒径小路,边走边问,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小村。而后问到衢州中学教师办公室,欠身向看门人问道:“贵校有位查理先生,在办公室吗?敝人是《东南日报》记者,因事从金华到衢州出差。现在,我是从衢州城里专程前来拜访他的。”
那位看门人抿着嘴笑道:“这里是有个查理,可他是学生,并不是先生。”
陈向平一听,大为惊骇。他脑海中时隐时现的那个老成持重文人的身影,顿时变成了一个满脸稚气的少年模样,似乎他原先的意想这时全乱了套了,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央求道: “啊!查理不是先生,而是个学生,那,我更想见见他。”
三
金庸,一个方脸宽额却又瘦骨嶙峋的十六七岁的学生,终于被领到办公室来了,让他和这位远道来访的老记者先生见面。请想:他们两人素昧平生,从不相识,年纪又相差二三十,初次晤面,还会有什么共同语言?谈些什么?又从何谈起?
万没料到他俩这次会晤,却是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契,彼此都感到相见恨晚。这事在当时的衢州中学和《东南日报》都曾传为美谈,众口赞叹不已。古人以文会友,并不乏例。但现在一个弱冠少年,只写了几句文章,竟逗得一位资深记者如此神魂颠倒,思绪不宁,直至最后还要踽踽独行,躬身趋访,有似朝圣拜佛,这确是世间罕见之事。
1941年底,日本突然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日海战愈战愈烈。次年夏初,沪杭日寇更加狂妄,调兵遗将,一心要攻占金华、衢州等地,以打通浙赣铁路,企图牢固控制从上海到广州以及印度支那半岛的陆路交通。
局势紧急,《东南日报》仓皇从金华迁往福建;而衢州中学也不得不向山区转移。为了减轻旅途中过多的累赘,学校在出发前,想方设法丢掉一些可以丢掉的包状,决定尽早让毕业班学生提前毕业,这就使金庸成了“早产”的高中毕业生了。
他很想升学,但挑来拣去,对当时闽、浙、赣一带的几所大学,都不感兴趣。由于那时我国文化重心西移,最后还是决定跟几位同学结伴西行,匆匆奔赴内地投考大学。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就在这兵慌马乱、小百姓纷纷逃难之时,金庸竟在漫漫旅途中又和那位老记者陈向平先生不期而遇了。故人重逢,喜出望外。无奈流亡途中不能久聚,当晚,就在陈先生下榻的旅店里,二人关起门来促膝谈心,自上灯时分一直谈到翌日天明,仍嫌言未终,情未尽。人生难得一知音,金庸为此写了篇《千人中之一人》。这篇文章登在《东南日报》分上、中、下三天连载,文词委婉亲切,至为感人。他俩这次旅途邂逅,遽逢而又遽别,陈向平南下福建,金庸要去四川,可谓南辕北辙,从此彼此越离越远了。
金庸和同学们拾路继续汲汲西行。一路上,车船十分拥挤、步行又很缓慢,身边盘缠也不足,最可虑的是内地大学的考期却很逼近。心想:当年是万难如期赶到参加考试了。
四
金庸处境困窘,真是进退维谷,因他没有经济来源。仔细想想,觉得还是和同伴们暂时分手较好。于是,他单独一人转到湘西一个同学哥哥的私人农场去工作。论头衔是农场主任,独当一面。其实也只是在茫茫飘泊之中,惶无定所,暂时找个栖身之地罢了。直到第二年夏天,他才从湘西负笈前往重庆。正好赶上考期,考进了中央政治学校。他读的是外交系。
两年时间,历尽艰辛,跑了近万里路,到了重庆,在学校,却只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书。1944年,秋末冬初,盟军对法西斯战争的已经胜利在望,国民党遽然一个劲儿鼓吹“反攻,反攻”,大张旗鼓地开始招兵买马,声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次主要是招募大中学生,即后来所谓美式装备的“青年军”。
金庸所读的中央政治学校,在这次招兵中规定:所有学生,不论哪个年级,也不管什么科系,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后审批。这是国民党官爷们搜肠刮肚,挖空心思,苦想出来的似有民主色彩的巧妙手法。这种手法妙就妙在毋须强拉硬拽,就能请君乖乖地自动入瓮,上下不伤和气,是一杯“敬酒”。可金庸偏不报名,拒不参军。后果怎样呢?那还用说,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
凡是抗战时期到过重庆的人,大都会有这样一个同样的看法和印象:那时在重庆,对于一个流亡学生来说,读书和吃饭几乎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两者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有书读,才有饭吃。学校是读书的场所,同时也是吃饭的地方。所以,离开了学校,失学还只是小事,而丢失了吃饭地方,那就要挨饿,这可是大事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经过熟人的介绍,他有幸进入当时藏书最多的中央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馆长也是浙江海宁人,和金庸算是小同乡。倘若寻根究底,他们还沾点亲呢。因此,金庸能在中央图书馆谋得一个职位,也还不能说是无缘受爵。
那他在图书馆倒底干啥事呢?无甚要职,只是管管阅览室。每天上班,捧本书坐在阅览室门口,见人进来,努努嘴,示意请他拿个阅览牌;看人出去,要他将阅览牌丢下。那时并不时兴什么工作证或身份证,衣冠楚楚就是好人。所以,管阅览室也就没有收证、验证、退证之类的麻烦。还有别的什么行当差使比这更轻松的?他金庸也算倒运之后又碰上好运了。他每天都可以读他的《资治通鉴》或英文诗选。
五
那时重庆有家杂志,叫做《时与潮》,内容多是从外国书报上翻译过来的小说、散文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特写,还有各种趣闻和名人轶事,颇受读者欢迎,销路不错。金庸见《时与潮》风行一时,禁不住跃跃欲试,也想办个什么刊物。在那时要办刊物,他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于是便邀了三位中学时代的同学合伙,创办了一种月刊。鉴于美国有本著名的《大西洋杂志》,因此就取名《太平洋杂志》,指望以刊名相似而引人瞩目,以广招徕。
《太平洋杂志》主编之职,当然非他金庸莫属。他不但有主编能力,且也有编写时间。他每天上班,一边照顾阅览室,一边顺便编写他的杂志稿子,身边参考资料又方便,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得其所哉。挨到下班,他又随身带上一本英汉字典,匆匆赶到美军俱乐部去,抢译新到的外国书报。这个俱乐部正好也在重庆两路口,离中央图书馆不远。那里外国报刊的来路非同一般,全是由美军飞机直接空运去的,所以要比重庆任何单位买到的外国报刊都早得多,要闻趣事贵在一个早字,越早越好。迟了,人云亦云,成为陈词滥调,读者就厌腻了。
《太平洋杂志》的文章,不论写的还是译的,尽管笔名张三、李四、王五篇篇不同,其实,极大多数连同发刊词都是他金庸一个人的手笔。自己的作品为何不签署同一个笔名?他的想法是:一种刊物既需要广大读者,也该拥有很多作者,最好不要让人看成是本个人文集,刊物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是重要的。
没有资金,怎么印刷?变卖衣物么,他们只有这冬天正穿着的一身破旧,如何卖法?到头来,免不了托亲求友,好话说尽,转请出一位同学的亲戚的朋友担保,才得在重庆大东书局赊印了3000本。
这样依靠间接又间接的关系,仰人鼻息办杂志,怎能长期维待?第一期虽然以“正在申请登记中”的名义出版了,3000本也几乎全部售完了。可第二期,大东书局死活不买这个帐,无论如何不肯赊印。因为当时纸价飞张, 赊印肯定是赔本的。《太平洋杂志》告贷无门,它的创刊号也就成了停刊号了。
六
正在这时,那位很想成为桐油大王的湘西农场场主,因事千里迢迢从湖南到重庆出差,这位场主非常赏识金庸的才华,这回又礼贤下士,敦请金庸再到湘西去为他经管那个私人农场。他慨然提出:只等农场开垦出来,种上了油桐树,就送金庸出国留学,金庸也不是个计较一时薪金报酬的人,只求有个陪伴,要带我同去,待遇也和他一样,这也是有待农场有了出息以后的事,算不上苛求。所以双方毋须讨价还价,也不必立据订约,只是君子协定,开诚布公几句话就谈妥了。我们又没有什么细软或大包大件要的打点的,两人只带一卷铺盖一只箱,说走就走。金庸很快办理了图节馆的离职手续,就轻装简束启程去湘西走马上任了。
读书是金庸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在学校里,他是学生,学生的本职就是读书;进图书馆,有空他也同样看书;现在来到了这个荒凉的农场,闲暇时间,他仍手不释卷、孜孜不倦地读书。他是个一目十行的人,虽然初来农场时,从重庆带来了一些大学课本和参考书,但没过多久,不论英文版还是中文版的,他全都读了,有的温故而知新,还看了第二、三遍。
在湘西这个荒山野岭地方,无书可买,也无处可借。到后来,百无聊赖,他只能动手译书以自娱了。1942年那回在农场,他试译了一部分《诗经》。这次是按初来的计划,编译《牛津袖珍字典》。这两次翻译都是半途而废,未能译完,固然是憾事。但在翻译中掌握了大量词汇,使他的英文有了更扎实的基础,这对他日后的创业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是1945年5月初去湘西的,过了3个月,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了,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全民狂喜,举国欢腾。抗战开始时,从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逃到湘西去的那些难民,在内地被称为“下江人”的,这时沦陷区光复,个个归心似箭,成群结队陆续离开湘西,都要“打回老家去”了。
金庸眼看着这副人群大回游的情景,方寸已乱,初来场时的信心渐渐动摇了。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垦荒植桐极其艰难,而留学的希望也很渺茫。挨到第二年初夏,金庸再也不愿在湘西这个荒山野岭的地方呆下去了。他终于辞去了农场里的职务,要返回阔别已久的海宁老家去看看亲人了。
七
这个离家多年的游子姗姗归来,一个战乱离散的家庭终于团圆欢聚了。他那鬓发半白的父亲翘首企足,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当然欣喜无比。后来得知这个出门已有十年的儿子并非学成而归,而是被学校开除而辍学,后来虽在图书馆和农场工作将近两年,但也只是勉强糊了自己一张嘴。且不说没挣到什么钱补贴家用,就连自己换洗的衣服还欠缺呢。简直是一无所成,也一无所得,毫无意义地虚度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呢?
做父亲的不由得忧心忡忡地问道:“还要从大学一年级ABC读起?这也太轧闷(纳闷)了。”话音是相当悲凉的。
金庸低头听着,一时哑口无言,只是苦笑而已。兄弟姊妹10多个,他排行第二。除了大哥、大妹已成家分居,其他弟妹都要家里抚养,小的在吃奶,大的要上学,这对一个久遭日寇洗劫的小康之家,谈何容易!
在这失学失业而闲在家的时候,金庸脑海中的那些悠悠往事活动了起来,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东南日报》的老记音陈向平,“啊!他可不可能……”
《东南日报》在日本投降后,早已搬回杭州。金庸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写了一封信给陈向平。
陈向平接到了来信,竟义不容辞,欣然应允荐金庸进《东南日报》工作。自从那年旅店分手,屈指已五年了。而金庸正正规规在大学里读书,却只有一年零两个月。金庸在信中已说明了自己的这些坎坷经历。但这位堪称伯乐的陈先生坚信自己当年见过的这匹马,家养的时间虽短,可这几年来,一定会自食自饮,扎扎实实吃了大量肥嫩的野草,吸收了充足的营养,现在更是膘肥体壮,很可能是匹千里驹了。
果真不负陈先生厚望,金庸进入《东南日报》,迅即脱颖而出。报馆安排他做的是翻译工作,晚上八点,听译伦敦广播电台的新闻。那时,报馆里还没有录音设备,要听译国际新闻,只靠一台收音机,一边听,一边写下几个字,听完以后,要凭记忆,并借助自己写下的那几个关键性的字,把刚才听到的新闻直接译成中文。好在他反应灵敏,记忆力强,中英文都好,忆译起来,得心应手,干净利索,译文几乎下笔不改,自也毋庸眷清,可谓一气呵成。这样,他一天的本职工作就轻而易举地干完了。
八
我问:“外国电台广播,说话这样快,又只是说一遍,当时无法核对。能听懂,已很不错。怎么还能逐字逐句直译下来?”
金庸道:“一般说来,每段时间,国际上也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连续性。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事件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不大有差错。”
他每晚收听一刻钟伦敦广播,连听带译, 一般不超过三十分钟。白天没有什么工作,自然十分清闲。后来,他自己提出在报上主持一个《咪咪博士》专栏,声称能为读者解难释疑,回答任何问题,就是古今各种奇案怪事,也都有问必答。我笑道:“那要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还要博览古今中外,精通医药工农、诸子百家,三百六十行,行行都会,你比诸葛亮还‘来斯’。”
“可以查查资料,翻翻百科全书嘛。每天读者寄来那么多信,提出无数问题,即使能答,也无法全答。只能挑选几个普通人比较感兴趣的,在报上解答一下。这样,一般人就认为《咪迷博士》达古通今,无所不知了。”他接着又微笑道:“说来好笑,想不到当了几天《咪咪博士》,我在杭州竟混出一点小名气了。”
晚上听译伦敦新闻广播,白天主编《咪咪博士》;可令人惊奇的,他整天还是显得相当空闲,自由自在自己读读书,看看报。他看报又是中外兼顾,大小不分的,连小报的副刊也要浏览一下,有时还邀伴上街喝咖啡,学跳舞。他也到该找对象的时候了。
西湖虽好,却非他久留之地。1947年,金庸接受了《时与潮》杂志社的聘请,贸然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杭州,转到十里洋场上海滩去了。
抗战时期的《时与潮》可以说是重庆最畅销的杂志。日本投降后,《时与潮》也和其他一些内迁单位一样,想方设法回迁,迁到了文艺人才荟萃的上海。国民党立法委员邓莲溪当了《时与潮》的后台老板。但这时的《时与潮》已难以在上海滩独占鳌头、稳执牛耳了。上海的报刊更是花样繁多,可谓群雄并起。
不过,邓莲溪的神通广大非凡。他为《时与潮》搞到的房子,那是特等超级的,是抗战前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成的公馆,巍然一座铁门高墙,并有花坛草坪的花园洋房,坐落在梵王渡路。
九
据说这幢三层楼房当时价值五百多根金条呢。《时与潮》的编辑部设在楼下最南面的一个豪华的小客厅里,客厅呈圆形,周围是厚玻璃板墙壁。
1947年冬,有一天,我路过上海,特地下车去看望金庸,只见他一个人,单独坐在那个圆形编辑室里,不慌不忙从一大堆新到的外国报刊里挑选文章,先剪下来,分寄给各个特约译稿去译。待那些译文寄回来后,再由他核阅修改。他名为主编,可手下并无其他编辑协同工作。因此,这个半月刊实际上只是他一个人包干,完全由他独立支撑。
我问:“你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邓莲溪和你又不熟悉,他怎会打你的主意,把你从杭州拉到这里来?
“不瞒你说,我为《时与潮》曾经翻译过一些文章。大概看我的动作比较快吧。在杭州《东南日报》时,我一收到这里寄去的原文,先看一遍,立刻动手翻译。一、二千字的文章两个多小时脱稿,一般不需要眷清重抄,当天寄回。这样译了一些时候,不知怎的,《时与潮》后来便聘请我。而我也觉得上海新闻界、文艺界比杭州活跃得多,所以就决定接受聘请来上海了。”他说话仍是不快不慢的,脸上带着笑容。他是相当自信,可并不显得自满。
那个邓莲溪可说是个精透得近乎悭死的人。那座花园洋房,我看见有几个高级套房被封锁起来空着。金庸是为他邓老板的《时与潮》撑台的唯一主编。他却只让金庸住在阁楼上,真是太不像话。
金庸转到《时与潮》不久,也像是时运亨通,适逢上海《大公报》缺人。他又进而在《大公报》兼任了记者,那时的《大公报》与《申报》《新闻报》并称中国三大报纸。而《大公报》的品位还略高一点,更受知识界欢迎,在舆论界也更具有权威性。可有一点还要说明,金庸这次进《大公报》,既非应邀受聘,更不是托情说项,而是硬碰硬。完全凭真才实学,正正规规考进去的。《大公报》那次招收记者,是公开招考,报考者200余人,其中不乏大学新闻系、中文系本科毕业生,本埠外地的小报记者想来跳槽转户的,也大有人在。最后揭榜,仅录取了金庸一人。他从此在《时与潮)与《大公报》两处同时兼任编辑,工作起来,好像也并不显得怎么忙累,都还是胜任愉快的。
十
我问:“《大公报》和《东南日报》比较起来,觉得怎样?”
他道:“那《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了,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互相商讨,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错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说到这里,他又掉转话头,微笑着说:“嗯,《大公报》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拆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氽花生米之类,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停了一停,又说:“《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称为‘记者’,就是报馆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
1948年上半年《大公报》开始增出香港版。金庸被派往香港工作。因去港以前,曾在上海大操大办结了婚,借了不少钱,到香港后,业余时间便拼命写稿还债。五十年代中期,他接受了另一家港报的特约,开始试写武侠小说,那头一部就是《书剑恩仇录》。这部小说后来在香港拍成电视连续剧,后又拍成电影,即《江南书剑情》和《戈壁恩仇录》两部有连续性的姊妹片。后来,他写的其他小说也都先后搬上了荧屏。
1958年,他离开了香港《大公报》,应聘到一家影片公司当了一段时间的编剧和导演。内地曾放映过他编导的《王老虎抢亲》,这部影片用的是笔名“林欢”,有时又干脆映出正名“查良镛”。
不久,他又离开那家影片公司,改辕易辙,自砌炉灶,创办了香港《明报》。《明报》最初每天只出一小张,几个月后,便改为一大张,由于金庸思路敏捷,中英文均佳,他几乎每天都阅读相当多的中外书报;听译外国新闻又是驾轻就熟,这就使他在捕捉国内外新闻方面既广又快,胜人一筹;他又擅撰社评,再加上他自写的武侠小说连载,这样,《明报》的内容可说是包罗万家,雅俗共赏,销路越来越大,广告日多,而其版面也一增再增,很快就增至七八张,后又进而改为彩色印刷,并采用电脑排印。
十一
后来,《明报》发展成为明报集团有限公司,除了出版《明报》日报,还有《明报晚报》《明报周刊》《明报月刊》《明报》北美传真版,此外,又开办了颇具规模的《明报》书刊出版社。但在1986年,金庸来南京时,却说:“报纸无钱可赚,多靠广告收入,这段时间,《明报晚报》老是亏蚀,我打算停办。”果真,《明报晚报》只拖了两年多,最后还是暂时停刊了。
金庸办报,成绩卓越,几十年来撰写了很多社评、剧评、散文、传记,又写了武侠小说十五部,还翻译了大量文章,在香港,曾出版了《金庸选集》四十二部。他在文艺领域涉及面是很广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金庸自始至终激烈反对林彪、 “四人帮”。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金庸及其夫人和子女,一家四人,并和金庸单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邓还曾当面说他的《明报》有其“独特的见解。”而后,胡耀邦也邀见过金庸。1993年夏初,中央又邀请了他,江泽民也和他单独进行了交淡。金庸在香港确是位有影响的知名人士。
众所公认,金庸是拥有华人世界最广大读者的作家。每年版税收入2000万港元以上(不包括大陆),居华人作家首位。
由于学识渊博、著作丰硕,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高等学府的赏识与器重。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1992年上半年英国牛津大学遴选他为“访问院士”,邀他去牛津讲学半年,讲授中国小说和中国历史;1994年4月他先后荣膺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荣誉教授;同年10月,北京大学也颁授他荣誉教授你号,有的大学还开设了《金庸》课程,颇受学生喜爱。难怪有人推崇“金庸的艺术实践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
综而观之,如果说已故著名报人张季鸾是过去为国民党政学系吴鼎昌开办《大公报》的能人,那么,今日的金庸,更是凭他一支笔杆打开香港《明报》集团天下的奇人。香港人赞扬他是位眼光敏锐的企业家。他现年七十一岁,最近来信,他已于1994年1月辞去了明报集团董事长职务。目前尚“无固定的写作计划,研究方面的兴趣所在主要是中国历史”。“由于退休后摆脱了行政事务的羁绊,旅行的机会大概会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