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诗词隅见
金庸不善诗词,这点金庸自家曾经坦承,金粉亦少回护,而金黑多予攻击。格律不谨,对仗不工,是金庸诗词大病,不过,这只能证明,金庸不懂诗词之“学”,而并非不懂诗词之“文”。诗词之学甚易,只需几本工具书,二三时辰即可;诗词之文则难,不但要多年文字涵养,大概还要几分天分。
金庸作品中的诗词虽然都是借鸡生蛋,但对作品的确起到锦上添花之功,甚至对诗词原作,也有点铁成金之妙。
现略举一二,以资共赏。
立主脑
小说中的诗词,大概只能作为陪宾。喧宾夺主,自然是很不妥当的。即便不能如水底之盐,也绝对不能成为眼中金屑。小说中用诗词,如果不能彰显人物,契合情节,则只能沦为凑字工具,逞才捷径。
《神雕侠侣》一书中,伴随李莫愁一生的“问世间,情为何物”就极合她的身份。
其实,原著《摸鱼儿.雁丘辞》所咏的双雁,经历与李莫愁大相径庭。据词前有小序说“太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 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地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邱。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邱词》。”
雁雁情深,至死不渝,终以身殉。而李莫愁情路坎坷,中途遭弃。貌似毫不相关,但是其中的“欢乐趣、离别苦”却是一样的.“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于雁雁不过假想,自知受不了万里千山,形只影单,不如一同归去。在李莫愁却是实情,她的确尝尽孤独,无处可归。两相比较,这半阙词用在盗版的李莫愁身上,竟然比正版原文的雁雁更加适合。
下阙“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就与李莫愁隔得远了,因此果断舍弃。于诗词而言,的确残忍,对文章大势,却绝对称得上英明。《天龙八部》论珍珑棋局说:“段誉之败,在于爱心太重,不肯弃子;慕容复之失,由于执着权势,勇于弃子,却说什么也不肯失势。”老金其慕容乎?
剂冷热
心境有悲喜,词境有冷热。心境词境或严密契合,或参差对照,方显诗词妙用,否则,则沦为蛇足赘疣,大可舍去。
《射雕》第十三回《五湖废人》中,黄蓉陆乘风同歌一曲《水龙吟》。上阙回忆甜蜜往事,感“伊蒿旧隐,巢由故友”,悲“南柯梦,遽如许”,凄楚哀婉,则使黄蓉歌之;下阙 联系黑暗现实,恨“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愤懑激烈,则使陆乘风歌之,配以陆庄主剑拔弩张,往而不复的艺术风格,自然“激昂排宕,甚有气概”。 而作者用心之巧妙,引用之谨慎,均可见一斑。此为冷热契合之例。
或云金庸得享大名,实借助于影视。然而,《射雕》影视版本虽众,不过敷衍故事而已,至于文字之妙,能传十一者,实所未见。叹作者明珠投暗,编剧买椟还珠,而观者竞相以椟论价。
《神雕》中,杨过绝情谷念苏轼悼亡词《江城子》,可谓冷上加冷,雪上加霜: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是苏东坡悼亡之词。杨过一生潜心武学,读书不多,数处前在江南一家小酒店壁上偶尔见到题着这首词,但觉情深意真,随口念了几遍,这时忆及,已不记得是谁所作。心想:“他是十年生死两茫茫,我和龙儿已相隔一十六年了。他尚有个孤坟,知道爱妻埋骨之所,而我却连妻子葬身何处也自不知。”接着又想到这词的下半阕,那是作者一晚梦到亡妻的情境:“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料想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不由得心中大恸:“而我,而我,三日三夜不能合眼,竟连梦也做不到一个!”
妙在句句针锋相对,更妙在句句都能足尺加三。此时此境,纵然起苏大胡子于地下,也要自愧不如,甘拜下风:“兄弟,你的确比我惨!”
《神雕》开篇的采莲曲,竟然一曲之中,分出两种滋味。
唱歌少女“和歌嘻笑,荡舟采莲。”“歌声甫歇,便是一阵格格娇笑。”而闻者却心头思潮起伏,当真亦是“芳心只共丝争乱”。且喃喃自语:“那又有甚么好笑?小妮子只是瞎唱,浑不解词中相思之苦、惆怅之意。”
读至此章,感慨静安先生以“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论词,未免局隘。少年不知愁滋味,纵然歌出风月无情,离愁悠长,依然喜笑颜开,可谓“无我”;而历经 “悲欢离合总无情”的看客,即使只听见片言只语,却足以伤怀,又是处处有我。可知词之有我无我,不在词之章句,而在词之际遇也。
审虚实
兵法云“虚者实之,实者虚之”。
胡斐道:“怀中抱月,本是虚招,变为实招,又有何妨?”
愚以为,诗词的鉴赏准则和小说中诗词的鉴赏准则是大不相同的。诗词做时忌坐实,坐实则不空灵,失之笨拙。用时却必须切实,不实则流于浮泛。
若敷衍“英雄儿女”,空谈“侠骨柔情”,用之张三也可,用之李四也不妨,恐难称佳构。
但今人轮武侠诗词,多师从郭靖,原不辨诗好诗坏,要一看作者,二看字眼——想既是韩世忠所书,又有“征衣”、“马蹄”字样,自然是好的了。殊不知原作中“征衣”不过陪宾,“特特寻芳”倒是主旨——所以郭氏解读法的第三点,选择性失明亦不可少。
鉴赏诗词,拘泥于诗词背后的本事,实际上是限制了诗词的想象空间,对诗词的涵盖能力,是一种伤害。小说中引用诗词,则恰恰相反,如果不能使诗词切合故事,则失去诗词的意义,为小说中的蛇足。
《九张机》本无名氏作品,金庸擅自作主,将作者坐实,四张机指给瑛姑,七张机指给黄蓉。而“可怜未老头先白”,正是瑛姑遭遇;“无端翦破,仙鸶彩凤,分作两般衣”也合乎郭黄二人,被旧盟拆散的悲惨境遇。这作品冒的,似乎比原作者更有真实体验,更有著作资格,当然这不能证明她们更有版权:)
无故事的敷衍出故事,有故事的何妨变个故事。
宋仁宗的时候,吕夷简要退休了,皇帝说,推荐个接班人吧,老吕就推荐了陈尧佐。陈尧佐很是感激,带了酒肉去拜访,顺道写封感谢信:“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睹双飞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轻拂歌尘转。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吕很是承情,回答也很幽默:“只恐卷帘人已老。”
陈尧佐以燕子自况,表达了对主人“卷珠帘”,让自己得与凤凰为邻的感激之情,措词十分得当。
《天龙八部》中阿碧出场时也唱了这阕《踏沙行》。
阿碧身世阙如,不过可由阿朱的孤儿身份推知,她也是慕容家收养的。对于“主人恩重珠帘卷”的感激可知。而“凤凰巢稳许为邻”的感情,似乎比陈尧佐一味的感激要复杂得多。慕容是个骄傲的凤凰——阿朱也有这种感受,而自己不过是庭前燕子,一方面是对凤凰“许为邻”的感激,一方面是对身份地位差异的惶恐。“潇湘烟暝来何晚”,她和慕容之间,十余岁的年龄差异,更是无法弥补的差距。这一曲中,含了阿碧这么多的缠绵心事,难怪段呆听得荡气回肠。
阿碧是《天龙八部》中的小人物,着墨不多。我们无法揣摸她的凄凉身世,她的少女心思,她对慕容的暗恋情愫。然而,这阕出场时的《踏沙行》已注定了她对慕容的不离不弃。
陈作中,以燕子自比,不过随手擒来。阿碧身居燕子坞,比作燕子,自是眼前风光,较之陈大人的燕子似乎更实在些。
不过,凡事有度。《鹿鼎记》第四回《无迹可寻羚挂角 忘机相对鹤梳翎》以“羚羊挂角”“仙鹤梳翎”二招扣回目,使原来的比喻意义全失,又实在的有些过头了,且大有移的就矢之嫌疑。
重机趣
王小波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
诗有别才,无关学问。即便是学问,也应该是一门知情识趣的学问。奈何国朝文化破四旧后,萧条过甚,难免把小道的消遣,看得过于严重,甚至提拔到国学的高度。仿佛蓬门小户,无甚恒产,祖传溺器,亦当古董珍视。于是向故纸堆中胡乱抄的三五行,就可以被众粉丝捧作古文化传承者了。殊不知反露小家寒酸相。
反之,金庸的诗词有时用得未免太过“轻易”和“随便”。
譬如黄蓉用“碎挼花打人”来形容飞花摘叶的武功,用“魑魅魍魉四小鬼”取笑渔樵耕读,用“日之夕矣,牛羊下来”骂朱子柳,用《人入缸》词牌替换《风入松》,口角生风,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妙趣横生。
《鹿鼎记》的回目,是金庸向乃祖查慎行致敬的产物。按说,应当把它看得恭敬严肃才是。可是里面依然透露出金庸的一些“小淘气”。
譬如第二十一回回目“金剪无声云委地 宝钗有梦燕依人”,原诗写得是尼姑落发,没想到金庸径自提来,当了韦大人剃度的先声。真真应了“长江双飞鱼”的妙语:“和尚和尼姑是一家人。”尼姑既然 “正青春被师傅剃去了头发”,宝钗之流,只能梦里温存了,韦大人火烧藤甲兵,没了头发,现实中却依然有金钗来做SM道具,较之尼姑不知幸也不幸:)
第四十回回目有个小乌龙,目录中是“眼中识字如君少,老去知音较昔难”,正文中却变成了“待兔祗疑株可守,求鱼方悔木难缘”。无论哪个都是很有趣的,难怪金庸难以取舍。
“眼中识字如君少,老去知音较昔难”,本出《赠如皋许嘿公》,愿意自然是恭维许公识字多,《鹿鼎记》里却用来讽刺韦大人识字少。曾有笑话云,美国人说:“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是说中国队胜了;而‘中国队大败美国队’,又是说中国队胜了。总之,胜利永远属于你们。”而此处,识字多也是“眼中识字如君少”, 识字少还是“眼中识字如君少”。老美闻之,更不知所从。金庸能将汉字之奇妙,发挥得淋漓尽致,为武侠写手中仅见。(PS:炫耀“冰比冰水冰”的大虾隔壁去坐吧,这里没的辱没了各位的热血豪情。)
“待兔祗疑株可守,求鱼方悔木难缘”。此联包含了守株待兔、缘木求鱼两个成语,无须多说。有趣的是,这里的株和木,都有了具体的指代对象,就是那青木堂 堂主,韦小宝。写得是吴之荣这倒霉兔子,自己送上门,一头撞在韦堂主这根烂木头上,正好拿来讨好双儿,可怜吴之荣还指望着通过这根烂木头得好处(求鱼), 真是百日,做梦!《西游记》中,每以“木母”指代猪八戒,不知道金庸拿烂木头比喻韦小宝,有意?无意?
然,过于随意,亦有不妥处,譬如《躺尸剑法》中的谐音句子,为谑近虐,既俗且恶,焚琴煮鹤,美感尽失,我所不喜。但是,配合“铁锁横江”其人,又不能说不当。只是让人不由自主地郁闷:(
多科诨
“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
文字“收而不放则罔 放而不收则殆”。梁公文字,病在拘谨,收而不放。所以逗人瞌睡,全因少一科诨。
科诨不仅仅用于丑角,也可用于生旦,可用于《经》典,如段呆之歪解“臀无裤”,自然也可用于诗词。
最典型的当然要数《书剑》中,皇上嫖院的那阙《西江月》:
铁甲层层密布,刀枪闪闪生光。 忠心赤胆保君皇,护主平安上炕。
湖上选歌征色,帐中抱月眠香。 刺嫖二客有谁防?屋顶金钩铁掌。
两结尤其有趣,前面铺排得正大光明,庄重森严,到此突然一跌,大有三句半中那半句的风采。
拟御制诗“疑为因玉召,忽上峤之高”,深得“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而自注:玉者,玉如意也,玉皇大帝也,更令人喷饭。
《鹿鼎记》中,韦爵爷歪解顾炎武《心史歌》,竟然将“蒲黄”解释成“黄脸婆”,也是戏剧中丑角惯用的科诨手段。只是不知顾先生闻之,是感他全力回护,还是笑他不学无术,或是哭自己的文章明珠暗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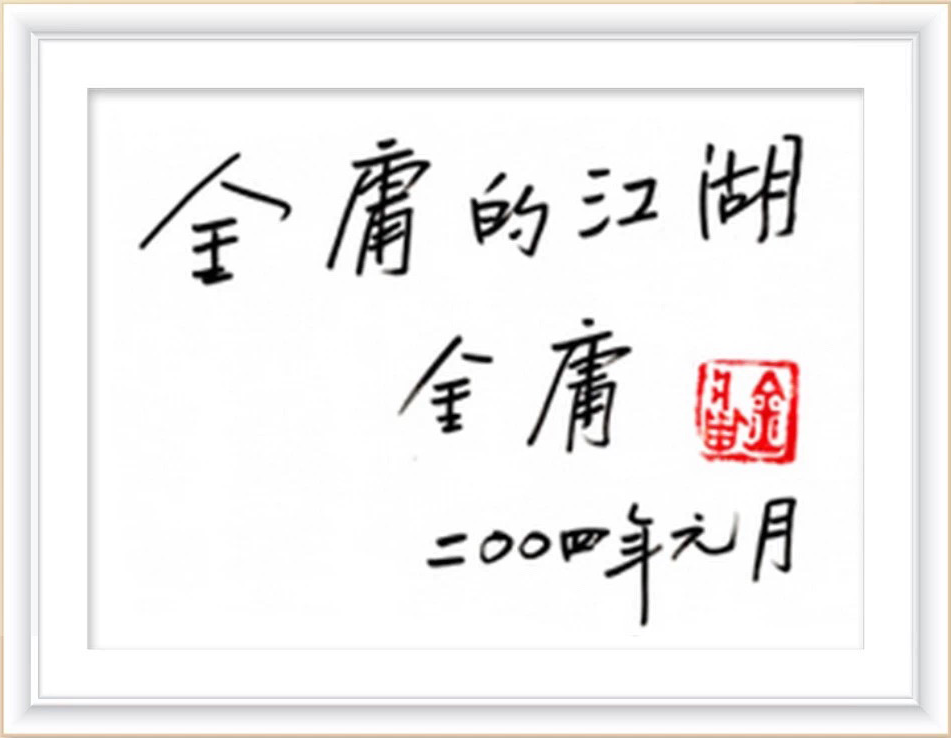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