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金庸、梁羽生诗词的人,往往强调梁羽生诗词创作的才华,而忽略了他在摘引前人诗词成句时的特色;往往强调金庸引用前人诗词时的浑化无痕,而忽略了他在诗词创作上的功力。
中国旧小说中,常常夹有诗词歌赋以及联句等韵文,尤其是明清章回说部,回目用对联、开场结束用诗词、散文中夹用损文,更是司空见惯之事。我这篇文章所说的旧诗词,实即兼指曲赋联句等韵文而言。它们通常用来描写景物、刻画人性、抒发情感、贯串情节,暗示主角的命运和故事的发展,在小说中自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
五十年代初期,所谓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崛起,这种夹有诗词韵文的形式,仍然廷续下来。梁羽生「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之中」,其武侠小说中大量应用旧诗词,自不待言,像被奉为武侠小说泰斗的金庸,也有不少作品使用了这样的形式。
所谓新派武侠小说,是相对于旧派武侠小说而言。它所强调的,不是打打杀杀的招术或武艺,不是诡奇多变的情节或故事,而是要有新的时代观念和新的文艺技巧。所调新的时代观念,是要求有反权威反传统的社会意识。所谓新的文艺技巧,是要求文字修辞去掉陈腐的语言,甚至从西洋小说或者电影中汲取表现的枝巧,来塑造人物,刻画心理。
这样说来,新派武侠小说所标榜的新文艺技巧,似乎与夹用旧诗词的旧形式有所抵触,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梁羽生、金庸等人的小说却还加以沿用而不革除呢?这牵涉到武侠小说作者对武侠小说观念的反思与演变,也牵涉到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
要谈这个问题,必须从一九六六年一月香港《海光文艺》创刊号的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说起。
《金庸粱羽生合论》一文,署名「佟硕之」所作,以往有人以为这是金、梁二人老友罗孚的笔名,一直到一九八八年柳苏(罗孚)在北京《读书》月刊写《侠影下的梁羽生》,才揭露了真正的执笔者,就是梁羽生本人。这篇文章比较金庸、梁羽生作品的异同,也分析了二人的优缺点,持论大致客观平允。例如说金庸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则有浓厚的中国「名士气味」;虽然二人都「兼通中外」,但金庸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而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虽然同属「新派作家」,但金庸的故事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妙,而梁羽生的写作手法则比较平淡朴实,虽有伏笔,却不够曲折离奇。可是,在比较分析的同时,佟硕之不但从武、侠、情等方面批评了金庸,说金庸的小说,写武功有时候过于离奇怪诞,写侠义有时候不辨忠奸正邪,写爱情有时候不顾是非礼义,而且,在谈到二人的文字风格时,佟硕之一方面肯定自己(梁羽生)的旧文学造诣,说能用旧回目、能写诗词的武侠小说作家愈来愈少,说自己对诗词的运用,是够水平的,一方面却对金庸的小说,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下列的批评:金庸很少用回目,《书剑》中他每一回用七字句似是「联语」的「回目」,看得出他是以上一回与下一回作对的。偶尔有一两联过得去,但大体说来,经常是连平仄也不合的。就以《书剑》第一二回凑成的回目为例,「古道骏马惊白发,险峡神舵飞翠翎」,「古道」、「险峡」都是仄声,已是犯了对联的基本规定了(《碧血剑》的回目更差,不举例了)。大约金庸也发现作回目非其所长,《碧血剑》以后诸作,就没有再用回目,而用新式的标题。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鵰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就是指《射鵰英雄传》中女主角黄蓉与「渔樵耕读」中的樵子唱答《山坡羊》一事。樵子所唱的三首《山坡羊》曲子,以及黄蓉所答唱的那首,并非金庸代书中人物所作,而是引自前人的作品。前者出于张养浩,后者出于宋方壶,二人俱为元代散曲的名家。据佟硕之的考证,《射鵰英雄传》最后以成吉思汗之死而结束,成吉思汗死于公元一二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因此黄蓉与那樵子唱答《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应该还在人世,时间当在一二二七年以前。然而,张养浩出生于一二六九年,宋方壶更在张养浩之后,试问黄蓉如何能识唱元曲?
【梁羽生毫不客气批评金庸】
佟硕之不仅紧紧捉住这个「宋代才女唱元曲」的「缺点」不放,而且进一步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多所针砭:
老实说……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令人惋惜。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我比较详细的指出他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事宝上,小说创作中引用前人的诗词,是不是要考据得这么严格,还有商榷的余地。不过,金庸一向爱惜羽毛,他对于佟硕之(梁羽生)的批评,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梁羽生和金庸曾是香港《大公报》系的同事,又是志趣相投的朋友,彼此非常熟稔,因此由梁羽生化名写的这篇文章,可以想见,招招攻心,记记击中了金庸的要害。梁羽生以「佟硕之」的笔名写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共两万多字,在《海光文艺》上,从创刊号起,连载了三期,而金庸应编者罗孚的邀约,却只在《海光文艺》第四期,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来作为响应。他自谦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只要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他之所以写武侠小说,只是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而已。文中他很含蓄地对梁羽生的批评,提出了辩驳。他说: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戏、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分辨是非。
这些话,可以说都是针对梁羽生的批评而发。梁羽生一向认为故事主题应该要非常鲜明,前后一致,要扣紧历史,反映时代,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写武功,不宜太离奇怪诞;写侠义要写典型英雄,形象鲜明;写爱情要发乎情,止乎礼。这些要求,都合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大概没有人反对,但写武侠小说要是处处受到这拘限,恐怕梁羽生自己也不容易做得到。即使做得到,也不容易感动读者,引起共鸣。《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发表时,金庸的《天龙入部》尚在连载之中,书中的「六脉神剑」,剑气可以杀人,已足够令梁羽生匪夷所思,可以想见金庸后来所写的《笑傲江湖》中,像「吸星大法」之类的武功,甚至像令狐冲、东方不败之类的角色,一定更让梁羽生无法接受。不过,我们也可由此看出来,对于梁羽生的规诫或是批评,金庸后来的小说,在描写武功侠义爱情等方面,并未全盘接受。被称为金庸武侠小说封笔之作的《鹿鼎记》,主角韦小宝不会什么武功,人在正邪之间,情出绳检之外,更可谓是颠覆了武侠小说以武功为主的传统。这与梁羽生的观念都是背道而驰的。金庸以为写武侠小说,不必陈义太高,「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而应该生动活泼地去「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即使这个角色亦正亦邪,个性复杂,充满矛盾,也一样可以感动人,令人赏心悦目。无疑的,这种看法和五六十年代以后崛起港台等地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的观念是一致的。金庸变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也变成了他们模仿效法的对象。
我们再来看看新派武侠小说另一代表作家古龙。他在《长生剑》的「代序」《关于武侠》一文中所说的:武侠小说不应该只求诡奇神怪的情节,作者应该求新求变,转而描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古龙及六十年代以后大多数的港台武侠小说作家,通常强调的是人物的情感与个性,而非武功本身,他们通常不用联句回目,不多运用旧诗词,甚至不再注意故事与历史的结合,无朝代可记的作品多的是,而这个转变,金庸是一大关键。更明确地说,自从金庸的《射鵰英雄传》等书不用旧回目,改用新形式而获得读者热烈的响应之后,后来的作者可能是避难而趋易,也可能是迎合时代的潮流,多已舍旧而用新了。话说回来。金庸虽然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所著的武侠小说中,用实际行动在作品中否定了佟硕之(梁羽生)的若干说法,但我们却可以从下列事情,看个性坚毅好胜的金庸对老朋友的规劝之言,事实上是很在乎的。
【金庸在乎梁羽生的批评】
金庸的旧学修养当然不差,但相较于梁羽生的诗词造诣,他却一再谦称自己不懂平仄格律。他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书剑恩仇录》修订本的《后记》中说:
对诗词也是一窍不通,直到最近修改本书,才翻阅王力先生的《汉诗词格律》一书而初识平平仄仄。……本书的回目,平仄完全不协,现在不过略有改善而已。
像该书第一、二回的原来回目,被佟硕之批评不合格律的「古逍骏马惊白发,险峡神驼飞翠翎」,他就改为「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他又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说: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作诗填词我是完全不会的,但中国传统小说而没有诗词,终究不象样。这些回目的诗词只是装饰而已。
他一方面自谦不懂诗词格律,一方面却又肯定诗词在传统小说中的作用与重要性。金庸一向不自诩为新派作家,对旧诗词仍然觉得不宜放弃,所以在被佟硕之批评之后,他修改旧作时,除了增删故事情节之外,对若干诗词也作了修改。就此点而言,他可谓完全虚心地接受了佟硕之的意见。
金庸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旧诗词,大致说来,都是引用前人的作品,或配合故事情节的需要而改作。难得的是,金庸即使是援引前人的作品,也能够配合书中人物的活动,把这些诗词带引出来,而与故事情节融合无间。潘国森《总论金庸》比较金、梁诗词的时候,曾经举例就此加以说明。他说,金庸《倚天屠龙记》中引用了丘处机的一首《无俗念》,「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又说,《神鹏侠侣》中写郭靖吟诵杜甫诗句时,写郭靖记性不好,只记得「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等句,「完全合乎郭靖的天资」。潘国森说得不错,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论述金庸小说中的诗词歌曲,也举例说:《书剑恩仇录》第一回,写武当派名家陆菲青,策马在塞外古道西风中,吟唱起辛弃疾的名句:「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首(宏一按:首应作头)万里,故人长绝……」,以为「此词正合书中意境,让人一读难忘」;又说,《射鵰英雄传》第三十七回中,写允文允武的丘处机,在赴漠北见成吉斯汗时,念了三首诗,说是「与小说的氛围及主题相吻合」,凡此都可以看出金庸在应用前人诗词时的高明技巧。
可是,潘、陈等人所说的,都是根据金庸小说修订本中的情节内容,假使我们拿原本来核对,结果会怎么样呢?以《射鵰英雄传》为例。这本书原是金庸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的作品,曾在《香港商报》连载。后来结集出版时,风行各地,引起东亚读者先睹为快的「射鵰战」。一九六六年佟硕之的文章发表之后,金庸于一九七五年修订了这本书的若干情节内容。他在该书《后记》中说:修订时曾作了不少改动。删去了一些与故事或人物并无必要联系的情节……也加上一些新的情节,如开场时张十五说书、曲灵风盗书、黄蓉迫人抬轿与长岭遇雨、黄裳撰作《九阴真经》的经过等等。我国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以说书作为引予,以示不忘本源之意。
可能是受了佟硕之的批评,反而激发了金庸的好胜不服输之心。他在修订旧作时,增加改作了不少回目与诗词,而且不愿意被只当做「洋才子」看待,不愿意只囿限于「新派」作家。他在修订旧作时,对与旧诗词有关的部分,似乎特别卖力。上面引文说他在修订《射鵰英雄传》时,「开场时」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情节,我就觉得改得很好,「古意盎然」。就这一点来说,更能突显出金庸在武侠小说新派旧派交替之间的关键地位。他不会「旧」到今人敬而远之,望而生畏,但也不会「新」到令人觉得浅薄,不值得回味。
可是,修订本真的处处都比原本好吗?
就旧诗词部分而论,似不尽然。我以为金庸可能太在乎佟硕之的批评了,尤其是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的讥弹,更使他如芒在背。因此,我以为有些不必修改的地方,金庸却勉强自己去改动。下面仍以《射雕英雄传》为例,来略加说明。
修订本《射雕英雄传》弟十八回中,说郭靖到桃花岛时,在积翠亭前,看到一副对联,写的是:桃花影里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
这一副对联,似乎很受读者欢迎。潘国森《杂论金庸》的《后记》中说,有一次他与同学任君讨论金庸小说,对方一发问,问的就是「桃花岛上积翠亭旁的对联写的什么」;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页二二一在讨论金庸联句时,也提到了这一副对联。并且说这「显然是金庸作的」。
我也以为这是金庸自己作的。这一副对联写得好不好呢?当然写得不错。除了「影里」对「潮生」尚有讨论余地之外,其它的字句可谓平仄合律、对仗工整。配合书中的情节来看,也可谓用得贴切稳当,颇能衬托出东邪黄药师洒脱而自负的一面。假如读者更细心的话,可以发现这两句诗,在修订本第十回「冤家聚头」中,又作「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萧」,对仗比较工整,「落」是要比「里」对得好。不过,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来,这一副对联在原本写的不是「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萧」或是「桃花影里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而是:绮罗堆里埋神剑,箫鼓声中老客星。
而且,这原非金庸所作,而是金庸抄引吴绮诗句而来。吴绮是清初名诗人,江都人,着有《林蕙堂集》。吴绮有一首题为《程益言邀饮虎邱酒楼》的七律:
新晴本色满渔汀,小憩黄垆画桨停。
七里水环花市绿,一楼山向酒人青。
绮罗堆里埋神剑,箫鼓声中老客星。
一曲高歌情不浅,吴姬莫惜倒银瓶。
沈德潜《清诗别裁》卷八曾径选了这首诗,并且评日:「三四语写山塘风景如画」。第三四句颔联写景,写虎邱山塘,果然「风景如画」,在人耳目。但我以为第五、六两句颈联写情,写客游落拓之情,也写得情味无穷,沁人心脾,令人低徊不已。就写情而言,允为佳句,丝毫不让上联二句。金庸摘引这两句诗,用在原本《射雕英雄传》中,写东邪黄药师尚未出场,黄蓉仅凭这一副对联,就可以在梅超风欲杀郭靖的紧张时刻,震慑住梅超风的心灵,可谓有先声夺人之妙。而且,这两句写情,写名士或是英雄在声色中消磨志气的落拓心境、惆怅情怀,也很切合书中东邪黄药师的为人行事风格。后来在原本《九阴真经》一回中又再次应用此一联句,同样令人赞叹不已。
那么,试问这样好的一副对联,为什么要改掉它呢?
原因应该是,和上文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一样,它犯了考据家所说的逻辑上的错误。在佟硕之的眼中,连张养浩等人的「元曲」都不能「唱」,怎么可能让故事背景发生在宋元之际的书中人物或情节,引用清朝诗人的作品呢?
可能金庸太在乎佟硕之的批评了,所以他后来在修订旧作时,努力学作诗词,更求精进,不但注意平仄格律,而且把这些怕有「常识以外的错误」的例子,也一并改换了。「桃花影里飞神剑」一联,根据吴绮诗句修改的痕述,颇为明显,问题是改得好不好。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者以为金庸小说的修订本一定比原本好,但我知道有些熟悉原本的读者再看修订本的时候,颇有怅惘若失的感觉。桃花岛上积翠亭旁的对联,原本的「绮罗堆里埋神剑,萧鼓声中老客星」,写的是落拓情怀,有倩翠袖愠英雄泪的感慨,有金剑沉埋、壮气蒿莱的悲怆,和重在写景的「桃花影里(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比起来,后者虽然和桃花岛的环境扣得更紧,但写得太飘逸了,像是描写超然物我的世外高人,而非有点落拓文士模样的东邪黄药师。因此,就这一副对联来说,不必讳言,我以为「新不如旧」。
也因此,我以为要评论或研究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应该只看修订本,应该和原本详细对照,或许对金庸及其小说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比较金、梁诗词的人,往往强调梁羽生诗词创作的才华,而忽略了他在摘引前人诗词成句时的特色;往往强调金庸引用前人诗词时的浑化无痕,而忽略了他在诗词创作上的功力。
【梁羽生摘引诗词成句】
罗立群《开创新派的宗师|梁羽生小说艺术谈》一书的《附录一》,由周清霖辑录了梁羽生诗词曲的作品三十一首,从中可窥见梁氏诗词创作的风貌。他在《七剑下天山》卷首代杨云骢所填的一首《八声甘州》,是常为人所征引的:笑江湖浪十年游,空负少年头。对铜驼巷陌,吟情渺渺,心事悠悠。酒冷诗残梦断,南国正清秋。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明日天涯路远,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数英雄儿女,俯仰古今愁。难消受灯昏罗帐,怅昙花一现恨难休。飘零惯,金戈铁马,拚葬荒丘。
这首词有人说「写得不坏」,我也觉得写得不坏,但我总觉得词中套用化用前人的成句稍为多了一些,像过片的头三句,几乎是袭用南宋末年著名词人张炎《八声甘州》下片的开头三句:「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尤其是「问谁留楚佩」以下二句,可谓一字不易。至于像「把剑凄然望」,脱化自苏东坡的词句「把盏凄然北望」等等,更不必一一指实出处。我很高兴读到龙飞立在《剑气箫心梁羽生》一文中,指出梁羽生被人称赞的回目创作,有不少是借用前人的诗句。例如:
「苍茫大地雄为主,窈窕秋星或是君」,下句采自龚自珍《秋心三首》。
「十年一觉扬州梦,万里西风瀚海沙」,上句尽人皆知,出自杜牧笔下,下句则采自纳兰性德的《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平楚日和憎健翎,天山月冷惜幽兰」,这是《掉戟沉沙录》中著名的回目,上句出自鲁迅。同样的,该书的其它回目,像「何须拔剑寻仇去,依旧窥人有燕来」,下句是黄仲则诗;像「九州岛铸铁伤心错,一局棋争敛手难」,上句是秋瑾诗。更有趣的,这三个例子,据说都是郁达夫曾经引用过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似乎值得喜欢比较金、梁诗词的人,作进一步的思考。
【金庸创作诗词有功力】
相反的,有些评论金庸诗词的人,看到金庸自谦不识平仄格律,就信以为真,以为金庸的诗词创作未臻理想,只强调金庸小说中的诗词,在引用前人作品时,如何如何运用巧妙,如出己口。这如同古人所谓矮子看戏,随人短长。事实上,金庸学柏梁体,用四十句古体诗,来做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又连填了《少年游》、《苏幕遮》、《破阵子》、《洞仙歌》、《水龙吟》五首词,来做为《天龙八部》的回目,在在可以看出他努力学习的成果和过人的创作才力。这些作品,虽然近于古人律赋或试律的写法,属于高明的文字游戏,但是也非常人所能。评论金庸诗词的人,应该看到这一点,才不致人云亦云。
我愿意再引一首金庸一九九三年担任香港基本法草委时的作品来作说明。此诗原为《参覃四首》之一,收在《香草诗词》第二辑中,系应其族长查济民之嘱而作,诗日: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
作者在诗前有几句说明:「我作旧诗的功力自知甚低,连平仄黏拗也弄不清楚,但长者命,不敢辞,半宵不寐,凑成了四首」。这段文字,不可轻易浏读过去。「半宵不寐」,就能写成四首七律,谅非一般人所能,而且他虽自谦「连平仄黏拗也弄不清楚」,但读者应可注意到他所写的诗,完全合乎近体七律的要求。这也是评论金庸诗词的人应该看到的。
上引的金庸这首七律,句句写实。从他早年南来香港、白手创业写起,然后说他创业有成、乐见太平之余,参与基本法草委的工作。他愿意不计旦夕之毁誉,而为百年大业竭尽志虑,只希望长辈能够时加策励。这样的诗,可能韵味不足,但用来叙事言志,却非常贴切。
说到这里,我愿意在此陈述我对金庸小说中诗词的一点浅见。我以为金庸小说中的诗词,不像梁羽生以抒情为主,而以叙事说理的居多,不管是出于他自己的创作或摘引前人的作品,这些诗词通常是用来描写书中的景物,或刻画角色的个性,或抒发书中人物的情感;它们随着情节的发展而自然呈现,随著书中人物的活动而充满新机能,它们变成了书中的一部分,读者不应只着眼于把它们独立出来讨论它们的出处。小说毕竟是小说,不要用做古典文献研究的功夫去苛求它。即使站在研究立场,探讨金庸诗词的来历,也应该注意及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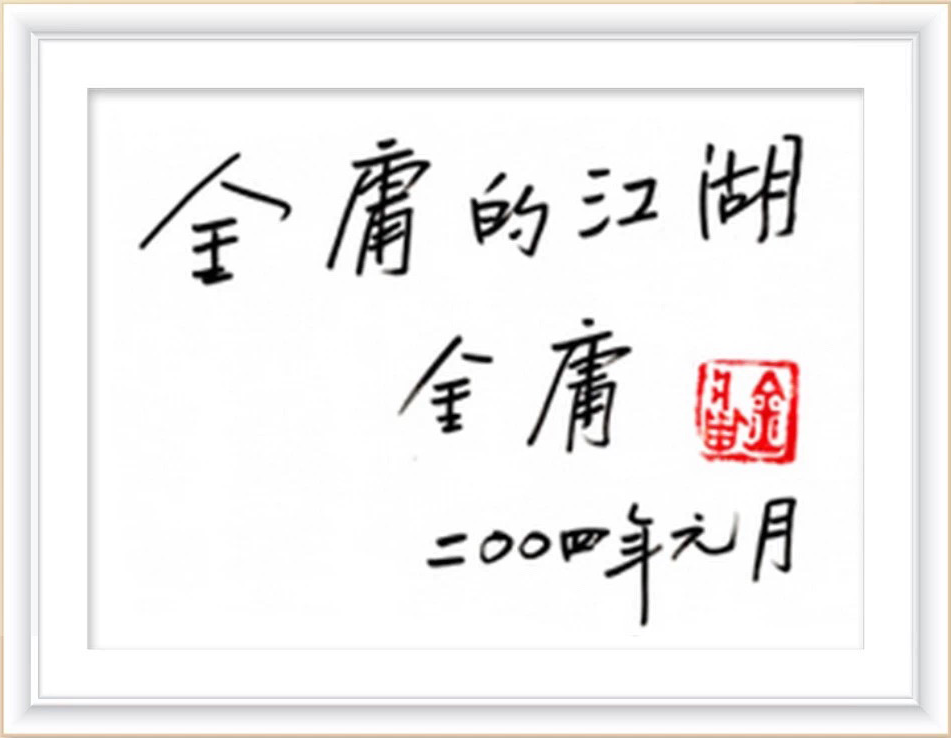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