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金庸晚年作为,多出于:【一】求名。【二】逐利。【三】民族主义。其中,一高于二。而三,绝不比一二更次要。说的,只是我的一点感觉。纯属臆测,绝无凭据。
一
查良镛先生,当他的早年与壮年,于小说创作、时政评论诸领域,皆曾坚守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时时处处,可见天才的闪光。越到老来,金庸身上的庸人气息越发浓重,甚至令人有些不敢相认,这个老人,即是当年查良镛?
“日暮而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查先生晚年,还谈不上“倒行逆施”,有些个颠三倒四倒是真的。最新事例,便是他的厕身中国作协。
查先生,老了。
老人,有老人的胡闹。
“不甘寂寞,趋时投机,自忘其丑,此甚足使人见之摇头叹息者也。……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老人)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病正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周作人《老人的胡闹》)
知堂此篇,指桑骂槐,说的是日本七十一岁的老学者山上参次,真意却在讥嘲老哥周树人。
此文此意,又未见得完全不适用于晚年金庸。1999年的金庸,于西子湖畔,发出了“新闻记者要向军队学习”的光辉号召,已经很有“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潮流”的味道了。
八十老翁何所求?金庸偌大年纪,仍是汲汲营营,不知贪图甚么?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仍见知堂《老人的胡闹》)
二百年前,金山寺,乾隆老儿遥望长江之上风帆点点,为之迷惑:“江中有船几许?”金山寺方丈答:“不过两船而已,一船为名,一船为利。”
二
时至今日,金庸的“为利”甚至“唯利”,已是尽人皆知。
但我从不认为金庸做事是将“利”字放在第一位。
虽然在1991年的香港富豪排行榜中,金庸仅列第64位,比他有钱的人多的是,但金庸所缺,分明不是“利”。
而是“名”——尽管金庸久已名满天下,而为华夏(非仅香江)其他任何富翁所不及。
三
1923年,向恺然先生以“平江不肖生”之名,发表《江湖奇侠传》于《红杂志》,万众争读,红极一时。其后,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火烧红莲寺》一拍、再拍……而十八拍。红,红,红……而大红!
可以说,现代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皆起步于平江不肖生。
平江不肖生,无名吗?
在获得巨大的俗世声名的同时,当日的所谓的文化界学术界,却对不肖生及他的小说视而不见,好像只有沈从文论及《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才认真评论过他这位湖南老乡。
二十年后,平江不肖生的名声,即已衰歇。到了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的时候,还在读《江湖奇侠传》的人,少之又少。
很巧合,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是在1955年,大陆正式禁绝武侠小说,也在1955年。禁绝之前,不肖生的读者已经不多。之后,当然就没了。
多年以后,老一代武侠作家的小说随金、梁、古作品的登陆而解禁。只是,今日,读过或想读《江湖奇侠传》的朋友,还有几个?
平江不肖生,有名吗?
四
古龙《欢乐英雄·序》:
“我们这一代的武侠小说大约是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至王度庐的《铁骑银瓶》和朱贞木的《七杀碑》为一变,至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又一变。”
享盛名于草根阶层,在社会上层默默无名;短期内声名大震,几十年后湮没无闻。
谁能保证:金庸,断不会步其先辈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之后尘?
金庸本人清楚吗?确定吗?自信吗?
五
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在遗诏中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
在《金庸,一捆矛盾》,我曾谈到:“从事于被其时代认为‘未入流’的文学品类的创作,而能及身见到自己的作品的经典化,金庸几乎是中外古今第一人。”
这固然是金庸的幸运处,同时何尝不是老先生烦恼的源头?因为,这一“经典化”,不是“完成时”,仍在“进行时”。基础已在,却又未尽坚稳。
金庸需要在生前尽可能多地抓住一些东西,以使自己(!)确信:金庸小说的成为经典,并不是他与众多读者论者的幻觉,而是经过了保险、再保险的。
金庸晚年之饵央视、入作协,皆可作如是观。
六
金庸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母亲,名为“徐惠禄”(后改“徐潮生”),金庸自己的母亲,名为“徐禄”。几乎可以肯定:金庸是以自己母亲的名字为处女作主人公的母亲命名的,表达的是作者本人对亡母的思念依恋。
《书剑》中,徐惠禄女士跟于总舵主的感情,很是暧昧。再联想到她的芳名,这事情其实越想下去越会觉得别扭。改名,势所必然。
此事,我在2007年的《 陈家洛:从“私生子”到“世家子”》已经谈过。结论:金庸写《书剑》时,只怕料不到多年以后还有这么多人读它,更没想到有闲人如我会细加推求。使用这个名字,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小小心意。
小说写了,发了,红了,之后呢?像《江湖奇侠传》一样,随风而逝……
1994年,在北大,金庸回答“武侠小说在你生命中的比重大不大?”的问题:
“实际上最初比重不大,我主要的工作是办报纸,但是现在比重愈来愈大。现在报纸不办了,但是小说读者好像愈来愈多,在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中国人当中,小说读者都很多,这是无心插柳了。我本来写小说是为报纸服务,希望报纸成功。现在报纸的事业好像容易过去,而小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成果。”(《金庸散文集》268页)
细细读来,应该可以体会到:当初金庸对自己的小说能得到这么热烈,这么普遍,(尤其)这么长久的欢迎与支持,是没有多少思想准备的。能有这样的结果,金庸觉得意外,也很开心。
金庸生平两大事功,武侠小说与《明报》企业,在他心目中一向主次分明,他还谈过:
“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
“《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以武侠小说享盛名数十载甚至可能延及后世,这在金庸,正是“不虞之誉”。得来意外,自然“高兴有这样的成果”,同时,也就信心不足。
冯其庸先生声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构思宏大、情节奇妙、语言优美、形象典型,……可与古典文化名著并驾齐驱”,这样说法,金庸信吗?
大有益于己,为何不信?
太出意外,岂能全信?
七
查先生早年,多经患难,可能因此而将钱看得格外贵重。至于有论者将“逐利”视为金庸做事之第一甚至唯一动机,此论,鄙人断乎不敢苟同。
多年来,金庸捐出超过5000万财产,以他的身家论,不算特多,也不好说太少罢?
我从不认为金庸将“利”字放在第一位,荦荦大者,以两事为据。两事,皆与《明报》相关。
1966年1月,金庸创办《明报月刊》。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彻底没落沉沦,几乎成了俄苏文化的殖民地(此谓“亡天下”)。人们对金庸的国学水准的估量不尽相同,谈到金庸对中国古典文化所葆有的那份温情与热爱,相信不会有太多人质疑。“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风雨如磐中,查先生创办《明月》,为了“保藏这些中国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此中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可敬而可悲悯的。
《明报月刊》被查先生定位为“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明月》盈利,投入《明月》。《明月》亏蚀,《明报》垫补。而《明报月刊》编辑部的房租水电等项费用,也全部由《明报》承担。这样不想赚钱也不能赚钱的刊物,怕不是很多的“文化商人”肯办罢?
时间就是金钱,查先生的时间,可能比你我的时间,更值一点钱。而当《明月》初创、胡菊人先生还没有接手主编之前的一年多,查先生为这份刊物投入太多时间精力。
到了今日,这个人,居然被想像成了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是否稍失公道?
《明报》企业的好名声,主要得自金庸的《明报》社评,以及《明报月刊》这份海外数一数二的高品质的学术刊物。
“自古文人皆好名”,这话,是金庸说的。创办《明月》,除了出于一份民族主义情感之外,自不乏求名之用心。如确,那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只要不损伤他人利益、不欺世盗名、不过分哗众取宠,即为大好。
某种程度上,正是几千年中才智之士们对于名声的渴望,推动着人类浩荡前行。
八
《金庸,一捆矛盾》,我说:“古来文人就没有不矛盾的,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如此繁杂而剧烈的矛盾冲突如金庸者,仍属罕见,一旦从金庸身上发现某一性格特征和思想倾向,我们立刻可以找到与此正相反的性格、思想也正存在于此人身上,且难分轩轾。”
这里,再试举一端。
金庸大方吗?金庸小气吗?
金庸,既大方,又小气。
吝啬的要死,慷慨的要命。
1991年,金庸终于将自己一手创办的《明报》出售予人。在于品海和他的“智才公司”之前,已有十家机构有意收购《明报》,其中一家,已备好了一张10亿港币的支票,考虑再三,金庸仍是未肯撒手。
金庸说:
“于品海出的价钱不是最高,连第二、第三高也不是,但我很乐意将《明报》的控股权交在他手里。……我们是真正的‘君子国交易’,他出一个价钱,我说太多,……终于在和沈宝新兄数度商议后,以折中的价格成交。即使再低价格,我也会欣然同意。……”
毕竟,只是金庸一面之词。
再看看另一方当事人的说法。于品海2003年接受记者专访,表示:
“最有趣的就是……本来我们估计要支付点现金,后来整个收购完成之后,不单是我们没有支付任何现金,还能够手上多了9000多万现金。”(见2010年9月《凤凰周刊》载文《于品海的传媒江湖》)
“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后世名?”如果金庸是这样的想法,那么出售《明报》,价高者得,他应该至少可以再多赚2亿港币(港币汇率其时远高于人民币)。
金庸大方吗?金庸小气吗?
既慷慨,又悭吝。
大方的要死,小气的要命(江湖上流传着许多关于金庸小气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金庸说自己“不想将《明报》卖给外国公司”,还是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怪。
金庸放弃厚利,未肯将《明报》卖予出价最高者,应有相当程度的“求名”因素。
金庸说:
“《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应当努力做对《明报》最有利的事。”
“(我的)第四个理想是,我创办了《明报》,确信这事业对社会有益,希望它今后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对大众做出贡献。”
金庸视《明报》如子女,望她独立,长命,有出息。
《明报》的存在,树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上面镌刻她的主要创办者,查良镛的名字。《明报》办得越久、越好,碑上的名字,也就越发如烛如金煜煜照人。
九
如有“今圣叹”,评点《鹿鼎记》,做得像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一样好或者稍差,是否也就同时证明了《鹿鼎记》的文学水准像《水浒传》一样高或者稍低?
我是如此揣测金庸亲身推动《金庸作品集》评点工作的动机的。
据说,关于评点人的确认、评点格式的推敲等等,金庸都有参与。
还是据说,金庸曾指示其版权代理机构(明河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对出版“评点本”的文化艺术出版社要优惠。金庸收取多少版税,不得而知,总是要比从“三联”收取的15%更低。
放弃一部分利益,促成评点进行,还是为求名罢?
果真如是,有些揠苗助长了。
一部杰作,得一高明的评点者,只可遇,不可求。《水浒传》问世约300年,这才有幸遭逢金圣叹。
好的评点,应是出于一种娱乐态度(娱乐时最认真最投入),而不宜看成一项工作,作为一项任务、期以两年完成 ,更是不妥。
十
金庸对着池田大作,畅谈97香港回归:
“一想到中国,立刻就出现‘庞大’的概念。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香港的九千多倍;十二多亿人口,是香港人的二百倍。我们投入这样一个大家庭之中,真正是前程无限,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业都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对于一项精打细算、小眉小眼的香港人,真像是‘小人国’的人物走进了‘大人国’,岂仅是《红楼梦》中的乡下女人刘姥姥进入富丽豪华的大观园而已。(笑)”(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看这架势,金庸在为(当时)600万港人代言?
他只代表他自己。
这段话说出的,是金庸自己的心声,得知其作品还有他自己可以回返大陆,那份难以遏止的兴奋之情。
金庸,从1979,一直兴奋到1997。甚至,金庸这里说出的某些感想,是他少年即已念兹在兹时刻在心的。
或谓“香港造就了金庸”,这是汉语汉字,我知道,我也都认识,却总感觉这话说的怎么就这么别扭?
诚然,如非1948年赴港,查良镛就不是金庸,然而,若不是内地“天渊翻覆”,查良镛又何止金庸?
读少年查良镛的几篇文章,很见得此子志不在小。未来从事什么行当尚属未知,至少,当时的他一直(很正常地)认为自己的舞台,在“庞大”的尧封禹域,“真正是前程无限,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业都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后来的发展,却是令人抱憾,无论他的小说写的多么好,他的《明报》办得多出色,有那么二三十年,金庸的影响力局限于香江一隅之地,稍稍延及海外华人群体。眼高四海如查良镛,以张良范蠡为楷模的查良镛,可能满足于此?
一种“补偿心理”罢?因为与“天下”隔绝得太久,当他终于可以再次“投入这样一个大家庭之中”,心情就格外迫切,事情做的,就格外急功近利。
港片中,有句话,常见的,“在狱中呆了三年,出来后,见个老母猪都觉得眉清目秀的”,金庸从香港进入大陆,有这股势头的。
一块钱,卖掉《笑傲江湖》,忒便宜啊?因为卖给的,是“中央电视台”,重点在“中央”二字。
为何加入“作协”?因为是“中国作协”,关键,在“中国”,金庸正要“投入大家庭”啊。
金庸,由“边陲”(香港),往“中心”(大家庭)联通;金庸小说,由“俗”,向“雅”移动。路,已经走了大半,还算顺利,不意却遭王朔中途邀击。
十一
王朔《我看金庸》,对金庸的触动很是深巨。之前,已有多人否定过金庸的小说,而金庸仍视“《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
很多人嘲笑金庸的回应中那句“八风不动”,我也曾讲过:“谈什么‘八风不动’?能做到吗?做不到的事,说来何益?”
鄙人看法,后来改变了。
有一种惯性思维,似乎一为“文人”,那他写出每一个字,都是在“做文章”。王尔德即宣称:“文学就是撒谎”。
然而,让我们平心而论,即是作为“职业诈骗犯”的文学家,偶尔也还是会说几句实话的。
感觉金庸“八风不动”之言,真实记述了他最初读到此文后的感受与反应,不是在“做文章”。
一个人,肯说实话,即使不应赞扬钦佩,也不致被嘲笑讥刺罢?况且,金庸只是说他读罢此文即刻想起了“八风不动”的佛家教导,又没说自己真能“不动”(原话:“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
若只感觉有微风拂面,需要提醒自己:我要努力做到“八风不动”?
王朔《我看金庸》,对金庸的触动甚是深巨。
王朔,这么厉害?
“黄蓉见他神色严重,道:‘这人很厉害吗?’洪七公道:‘欧阳克有啥屁用?他叔叔老毒物这才厉害。’”(《射雕英雄传·亢龙有悔》)
欧阳克后面,站着“老毒物”。矗立在王朔身后的,则是京畿那巍峨的城门楼,还有一座“纯文学”的老牌坊。
《九阳真经》教导我们说:“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无奈,理想太高,金庸自己也做不到。
面对王朔攻击,不能视如“风拂山冈、月照大江”,只因金庸,真气不足。
王朔连金庸的一部作品都没读完,作出的批评能有几多说服力?说服力虽弱,却是抓住了金庸身上与心上的最脆弱的两大“命门”。
王朔,身在近千年来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北京,不是很瞧得起一干“外省作家”,尤其是港台作家,
“只知道金庸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
这种论调,根本不值一驳,金庸居然不辞劳苦,列出一连串的好的浙江作家、香港作家的名单,累不累?
当年傅青主有数语说得甚妙,“讲学者群攻(王)阳明,……而阳明之徒不理为高也,真足憋杀攻者。”对于王朔的攻击,金庸的反应,自当以“不理为高”,如此,真足憋杀王朔。
金庸,太在意了。长久以来“沦落”在华夏文化的边陲,自卑感是有一些的。
金庸的另一“命门”,更令金庸感到自卑的,是他在文学上的“通俗”出身。
虽然王朔也曾被看作“通俗”,好在后来基本上是“扶正”了,这才有底气反戈一击,直斥金庸为“四大俗”之一。
如将金庸小说置于《红楼》群芳谱,更像哪位?
探春。
“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才自精明志自高”。
只可惜出身不正,乃是“庶出”。
一干“纯文学作家”,无论多么的不长进、没出息,好歹人家是大老婆生的,“我自一口真气足”!
十二
这些年,金庸飞来飞去,掺乎各方举办的各种“活动”,每到一地,例必题词,多为题写对联。坦白说,那些联语,拟的并不够好。
写对联,本非金庸所长。
几年前,看过某次活动的一位“主办方”成员的文章,说是在金庸到来之前,他们已经拟好了对联,金庸只管写字就好,哪知金庸竟不领情,自管现拟现写,引得这位先生大为不满,文章结尾悻悻然并且幸灾乐祸地说:他金庸自己拟的对联,也不好! 看了这篇宏文,令我作呕不止三日,到今天也还有恶心的感觉。
有些人,如这位先生,价值系统紊乱,竟将狗腿子拟稿大人物挥毫这种反常现象视作当然,在他们眼里,正常的,反成变态。
只可用自己的笔,写下阿猫阿狗代他拟就的句子,对于一个文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侮辱?
子曰:“唯名与器,不可假人。”真要丢人,也只可丢自己的人,如何将别人的狗屁对联算到自己名下?
话说回来,金庸何必丢人?这样的主办方的这样的体贴的态度,何苦再给他们写什么劳什子的对联?
李怀宇曾对许倬云讲说:“今天的金庸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不朽。”许先生的回答,甚为明快:“金庸的小说是划时代了,可以不朽。”(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192页)
如果金庸本人有许先生这样的确信,许多事(如:回应王朔),他应该不会做的,做了,也不致那样拙劣。
许倬云“金庸不朽”之论,别人不好说,王朔是一定不会赞成的。呵呵。
万里长城,无非是“把砖头码的长了些”,王朔的这一观点,我倒是举双手赞成。看八达岭长城,丝毫感觉不到有啥子“雄伟”,只有登上城墙,看墙砖上那些重叠凌乱的字迹,才让我深感震动:心中念中渴望“不朽”的,竟不限于一小撮人!
十三
一个人的学术或文学成就,与他的品德,不成正比。
王尔德以为:“内在美德并不是艺术的真正基础。”
乔治·奥威尔更是认定:“一个作家的文学上的个性同他的个人性格没有什么关系。”
奥威尔讲的,是狄更斯:“很可能,狄更斯在私人生活中的确是罗伯茨把他说成的那样一个麻木不仁的以自我为中心者,但是在他已出版的作品中,却隐含着一种与这完全不同的个性。”
奥威尔并不以弥满于狄更斯小说的那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从而断言它们的作者绝无可能麻木不仁自我中心,反过来说,即使狄更斯本人确实麻木不仁自我中心,奥威尔也不会因此断定狄更斯作品中那无远弗届的同情心尽为虚幻全是骗人。
狄更斯麻木不仁自我中心与否,很重要吗?会拉低或抬高他的小说?
奥威尔向来认为“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自然觉得罗伯茨《盲目崇拜的这一面》一书所写的“这些事情也不能否定狄更斯的作品的价值”。
我看金庸,在狄更斯与大仲马之间,比狄更斯低那么一点点,比大仲马,高那么一点点。当然,只是我个人私见,金庸小说的价值,不是我今天可以论定的,也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论定的。
百年以后,作者喑哑,作品说话。
再有一百年,关于金庸小说价值的争论,应该可以尘埃落定了。
如果作品是伟大的,不会因作者的人格缺陷而沦落。如果作品本身价值很低,即使作者的品格无比崇高,也无力哄抬他的作品,至于伟大。对小说家、剧作家来说,尤其是这样。
今天,金庸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的,无谓的,既不会拉升、也不致糟践他的作品。
一切,交付给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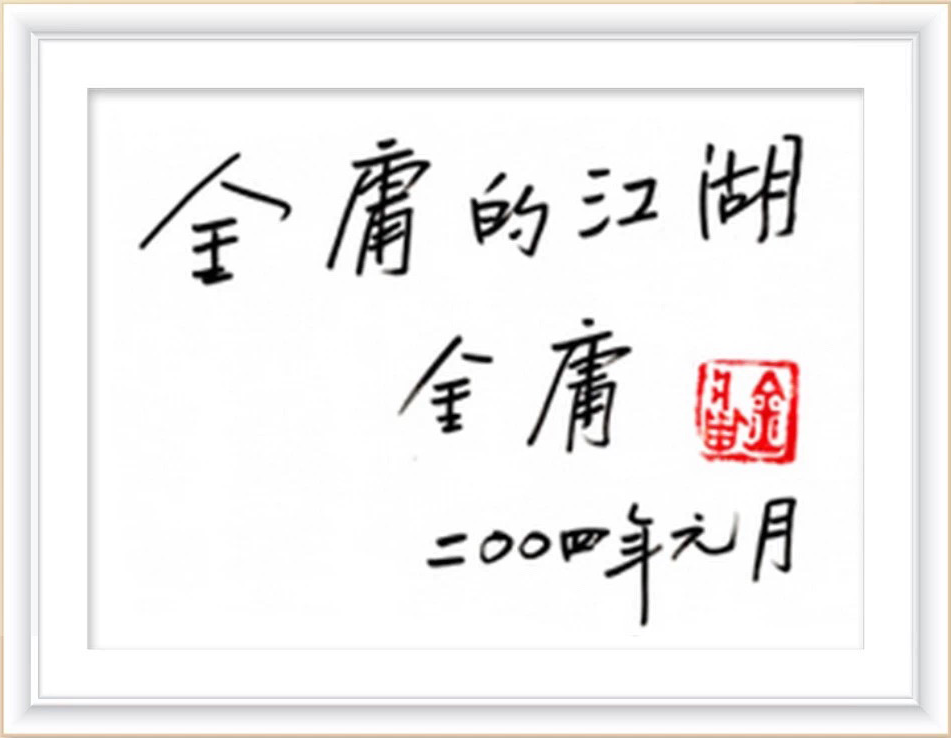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