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又向东行。他无牵无挂,任意漫游……
——《侠客行·第十二回·两块铜牌》
一
“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者,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缺陷”,是艾未未给自己预定的墓志铭。不特艾氏,多数艺术家、文学家,多少都有点“人格分裂”。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两种说法,都对,都不对。也许,将这两种相反的气质糅合到一处,才是一个完整的傅雷。
歌德借由《浮士德》,说:“在我的胸中,唉,住着两个灵魂,他们总想要彼此分离。”
有人指出英国思想家霭里斯“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话被周作人多次引用,周作人本人则认为自己的行为思想多由身上的“绅士鬼”与“流氓鬼”操纵。
弗洛伊德认为:“托斯陀耶夫斯基丰富的人格也许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神经症患者、道德家和罪人。”
金庸这个人,也是典型地、经典地具有“性格多重性”。
极复杂,又极其矛盾的一个人。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其性格,是太冒险的事。每个关于“性格”的词汇,用到金庸身上,鲜有不合适的,并且把这一词汇的反义词再“还施彼身”,同样甚至更加合适。
林语堂《八十自述》自称“我是一捆矛盾”。我最早看这本书时,就非常喜欢这话,后来读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90年写的《中国人的特质》一书,才知道这话的原创权不属语堂先生,而是明恩普。钱钟书也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这四个字,相信也是从《中国人特质》而来。
不过,明恩普说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指向全体,“中国人,是一捆(或译:一束)矛盾。”
金庸是典型的中国人,金庸是“一捆矛盾”,是“一束矛盾”。并且,金庸的这捆这束,比林语堂钱钟书的那捆那束,未见得更小些。
金庸髫龄即洞悉其父做生意的不精明,十五岁编写出版《献给初中投考者》,行销数省,因之我说“幼年的金庸宛似“天山童姥”:童稚的躯体包藏一颗世故沧桑的心。”,实则,金庸身上还有“天真、顽童”的一面,到老,也没改变。因为金庸商业上的成功,人们往往注目于他的精明世故,而忽视其天真、朴拙。一个通身精明世故的人,不会费尽心机去刻画石破天、虚竹、狄云、周伯通、李文秀这类毫无心机之人的。
并不是每个十五岁的中学生都会考虑到写一本书指导小学生如何考入初中自己从中赚取钞票,也不是每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都会因为对学校训育主任的奴化教育不满而在壁报上撰文把主任比喻成“眼睛蛇”的。第一件事金庸是1939年做成的,第二件事则是他1940年的丑恶历史。第一年,他是世故老人,第二年,又成了黄口小儿。好玩吧?
这张自发的大字报,最能表现少年金庸的勇气与狂气,更多是“傻气”。金庸晚年追忆此事,没有把自己拔高成“素质教育”的先行者,而是坦言“只是少年人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
太幼稚,太不成熟!说话办事不计后果,小孩子才优为之。1985年,龙应台眼中的台湾大学生是这样的:“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至于大陆学生,他方面素质是否优于台湾学生,我不深知,但在“懂事、老实、听话”方面绝对比台湾学生优胜,称得起是少年老成。
金庸这篇大字报,题目叫做《阿丽丝漫游记》,明显是模仿了英国作家卡洛尔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金庸所读《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按时间推测多半是赵元任先生的译本,扉页上录有《孟子》名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晚年金庸,世故滑头得很,但在某些方面,却也“不失其赤子之心”。
对于央视版《笑傲江湖》和评点本《金庸作品集》,金庸开初都是赞赏备至,过了不几日,又贬到一无是处,整件事金庸接近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实在大失风度,更谈不到精明。我们可以将此事解释为金庸利令智昏(傅国涌就是这样看的),不过我总感觉:说话不负责任,几分钟之前说的话,过一会儿就不记得了并且认定别人会像他一样不记得,这,是儿童的特权与特长。
记得傅国涌《金庸传》甫出,金庸老大不高兴,声言如再写小说,傅国涌必被写成反派坏蛋脚色(大意),我当时看了这则报道,直笑。
当年魏收奉旨著作史书,掌握了对时人及其父祖辈臧否论断的话语霸权,不免气焰高张:“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这倒与金庸的说法有三分相似,不过魏收的话,说给他人听,意在威胁恫吓,金庸此言,更多说给自己听,聊以自我安慰。少有魏收那种嚣张、恶毒,更多的是自欺和无奈。“《鹿鼎记》是我最后一部小说”,这话,有人是不信的,难道金庸本人,也不信?
记得我们小时候受人欺负报复无门时才会设想:在墙上写“张小强是王八蛋大坏蛋”(此即聂绀弩诗“儿童涂壁书王八”意也),或者在梦里想法子干掉他……
“我在浙江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人家说我学问不好,不够做院长。别人指责我,我不能反驳,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自己的学问。我向浙大请了假,来这里读书。”,这分明是赌气,在愤怒之外,听口气,看(访谈时)神态,有些个童趣盎然。
金庸在他的后期小说中,已经分明注意到了人性的极端复杂,书中人物,已非忠奸分明、好坏判然。但一直到晚年,提到现实中某位令他不爽的人物,“他是一个坏人”这样的话仍是常常脱口而出,心态与口吻,都很童稚化。
二
“在大部份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匪徒”,英国学者韦尔斯这句话,用到金庸身上,再合适不过。说穿了,“侠”,实近于“匪”。因为灵魂中住着一个“匪徒”,金庸自幼嗜读《水浒》以及武侠小说,到了后来,自己也写起武侠小说来。
1992年,凭藉着自己的十五部武侠小说,金庸获法兰西政府颁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法国驻香港总领事在赞词中称誉金庸为“中国的大仲马”。金庸为此“感到十分欣喜,……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以十二三岁时开始喜欢,直到如今,从不变心。”
大仲马声称:“历史是什么?就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这一态度,事实上为金庸所继承。“《三剑客》教了我怎样活用历史故事”,金庸与大仲马的故事总是与历史参合一处,他们所虚构的人物又和历史人物沆瀣一气,共同促成历史的巨大变故,可谓“贪天之功”,流风所及,虚构与历史也就混淆莫辨了。亦舒《胭脂》中的小女生陶陶对母亲讲说圆明三园的来历“玄烨——这便是康熙,鹿鼎记中小桂子的好友小玄子…”,小丫头对康熙大帝如此熟稔亲切,在在皆拜金庸之赐也。
从第一部作品《书剑》始,金庸几乎所有作品都有明确的时代印记。唯二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与《侠客行》。让金庸克制自己的“历史癖”,抛开历史背景来建构自己的武侠故事,想来是一件蛮痛苦的事。而《笑》《侠》二书居然没有历史年代,总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在。
那是因为:《笑傲江湖》是寓言。而《侠客行》,是童话。
《笑傲江湖》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中国自古“真理自上而下”,不管用过何种卑鄙龌龊手段,一个人只要掌握了权力,也就掌握了真理,同时成为了道德的化身,可以对贱民进行教化训育。《笑傲》则把这种政治、政客的真实嘴脸刻画入微,在读者面前呈现。令人警醒“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 。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笑傲·后记》),小说描写的时间跨度当然不会“上下三千年”,而是采解剖麻雀方式,从历史政治取一横断面来加以剖析、刻画,金庸自称:“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童话故事多数发生在一个模糊的“很久很久以前”,如果坐实小红帽出生于 1621年7月23日而美人鱼进化为人发生在公元前250年,这,毕竟是可笑的。
“阿绣嘻嘻一笑,说道:‘金乌派,嘿,金乌派!奶奶倒像是小孩儿一般。’”(三联版288页)
“年高德劭”的史小翠固然孩子气十足,说这话的阿绣本身就是一个16岁的孩子。其他人物,石中玉狡童,石破天懵懂,张三李四盲动,“不三”“不四”胡弄,“丁丁当当’?名字就很卡通。连书中的两位宗师级人物白自在、谢烟客,也尽显摇曳多姿,天真烂漫……
金庸每部小说都安排有福斯塔夫类型人物插科打诨,用以调节气氛,但对这么多大小孩子进行如此大规模总动员的,金庸出品,唯《侠客行》。
《侠客行》如万花筒,斑斓五彩,变幻无穷。
《侠客行》人物的平均智商,比金庸其他小说人物,低出十三点,还多。书中最工心计的贝海石其拿手之作也无非让石中玉充任帮主等着到侠客岛送死,这点伎俩拿到任我行、岳不群、戚长发等人面前,真正小儿科,不值一笑。
“摩天居士”谢烟客,其绝技为“弹指神通”,这一形象,与“东邪”黄药师应当稍有精神血脉关联。黄、谢立身都在正邪之间,都视道德规范如无物,都孤傲绝人,都受过爱徒的欺诓。谢的“弹指神通”比黄的“弹指神通”,功力相差无几,但黄老邪在诗词歌赋、诸子百家、医卜星象、音乐厨艺……方面的造诣,谢居士完全不具备。
莫非谢烟客正是童话版、卡通化的黄药师?
白自在、任我行、丁春秋、洪安通这几个角色在现实中的原型,差不多。都体现了一种“致命的自负”,面对属下的崇拜歌颂都有一种“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宽广胸怀,但,“威德先生”白自在比余子更可爱,在于他没有政治野心征服欲望,白自在更像是一个渴望被表扬被认可,得不到就乱发脾气、破坏性极强的坏小孩。
白自在毕竟也曾杀戮无辜,可他当时脑子有病!按照文明社会的通则,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不负刑事责任,只要能让陪审团相信罪犯脑子有病,枪击美国总统(里根),不也照样被无罪释放?
《侠客行》中多有杀戮之事,但我感觉不出浓重的血腥气。《侠客行》比金庸其他作品更明显是作者讲述的一个好玩故事,不是真的。小红帽和外婆给大灰狼吃掉也无妨,剪开狼腹,祖孙二人毫发无损。我读《侠客行》,跟读“小红帽”童话的体验,不差许多。
写作《侠客行》的金庸,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更纯净,更朴拙,以童心观照世界。
“此时日光尚未照到,林中弥漫着一片薄雾,瞧出来朦朦胧胧地,树上、草上、阿绣身上、脸上,似乎都蒙着一层轻纱”(三联版281页)这段话最堪概括全书氛围。
1998年,在科罗拉多大学主办的金庸作品研讨会上,金庸即席发言:“在希腊悲剧中,表演者常带面具,与中国京剧的脸谱差不多,脸上的表情看不清了,而幕后或舞台旁又有大合唱,唱的时候台上的对话暂时停止了,这就使观众和表演者拉开了距离。这一距离令观众意识到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故事,它与现实并不相等。”金庸认为武侠小说也有这一特点:“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与面具、大合唱的审美作用相似,它使读者意识到书中展开的是一个故事,与现实生活不同。”
所有武侠作品皆具此一特点,而《侠客行》,至为明显。
石破天这一人物,其天真处甚至令人追忆整个人类的童年时代。《庄子·应帝王》:“倏与忽(二人)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或许:石破天就是那天真未凿时的“混沌”?
最后,只有这个混小子破解了《侠客行》密码,得通大道,金庸在《后记》中以佛学解释:“大乘般若经以及龙树的中观之学,都极力破斥烦琐的名相戏论,认为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
其实,用道家思想也解释得通:“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小孩子,最柔弱,所以最有力;最缺少知识,因此智慧具足。
一个完全不通世务的文盲居然破解了《侠客行》猜想,满腹经纶的大师们皓首穷经却茫无所得,老子的解释是:“少则得,多则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三
《大英百科全书》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把‘荒唐文学’提到了最高水平。”
武侠小说的罪状之一,即是“荒唐”。《侠客行》则“更向荒唐演大荒”,使武侠与童话沆瀣一气,绝对是武侠小说中的异类,以前没有,以后?永不再有。
赵元任先生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序言中指出:“这是一部纯艺术的妙在‘不通’的‘笑话书’,是一部“哲学的和论理学的参考书。”(刘按:“论理学”今通译为“逻辑学”)
《侠客行》情节安排上的漏洞奇多,不通不通,然而你要把它当童话书看,不通也通。
《侠》书亦不乏哲思:“各种知识见解,徒然令修学者心中产生虚妄念头,有碍见道”(《侠客行·后记》)。
《侠客行》尤其是一本妙在“不通”的“笑话书”。金庸极具幽默感,每部书都有好玩好笑情节,不过也有为搞笑而搞笑的问题在,未免流于油滑。《侠客行》的幽默好玩则是神完气足,且贯串全书。
爱丽丝的两次“奇遇”,第一次从“掉进兔子洞”展开,第二次“奇遇”的开篇则是爱丽丝遁入镜子,进到了“镜子里面的房子”。《侠客行》主人公也曾遭逢两次奇遇。第一次,“狗杂种”与养母、黄狗失散,来在了软红十丈里,始与人间世接头,变成了“小乞丐”。第二次奇遇,“小乞丐”在谢烟客的祝福下,像神棍洪秀全一样,长时期发高烧,退烧之后,洪秀全摇身一变,成了主耶稣的二弟;而“小乞丐”,脱胎换骨,成了“长乐帮”帮主,石破天。
小说全部情节,皆由这两次“奇遇”(或称“错位”)肇始,着力描写主人公初入红尘“与世界接轨”的种种不适应、“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凿枘难合、“童心”与“机心”的龃龉倒错……石破天临渊履薄、战战兢兢,每句话每件事都说得做得严肃认真无比,而达到的效果,则是错乱梯突滑稽无比。
金庸写武侠,目的在于“自娱娱人”,归结到《侠客行》,“自娱”成分想必更多些,遥想金庸1965年,蘸得笔酣墨饱,写来酣畅淋漓,不亦乐乎?不亦快哉!
作为“武侠小说”,《侠客行》不是最佳,不够铁马金戈、惊险刺激;把《侠客行》当小说读,它绝对是第一流,别开生面,妙趣天成。其价值,至今未获应有的重视。
四
《爱丽丝游记》的写作风格,是金庸喜欢的路数,此书又是金庸童年所读,记忆深刻,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有意无意或多或少总有影响。
不过,我前面把《侠》《爱》放到一起评说,绝对不是要证明“金庸写《侠客行》时曾不断地翻读《爱丽丝》,照猫画虎而成”,无非以《爱丽丝》为参照物,试图阐明《侠客行》带有明显的儿童文学特质。
不过,我总怀疑现存《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并非全本,有一个章节佚失了,幸好书中一首诗透露出些微消息,助我追觅到蛛丝马迹:
“本来都是梦里游,
梦里开心梦里愁,
梦里岁月梦里流。
顺着流水跟着过——
恋着斜阳看着落——
人生如梦真不错。”(赵元任译)
诗中梦里,爱丽丝到过一个地方,有流水、有斜阳,而我们分明记得“桃花岛”上,潮水怒生,日影昏黄,有诗(联)为证:“桃花影里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
据此,我推断《爱丽丝》的一个章节佚失了:小顽童爱丽丝曾经“梦游”至南宋年间的桃花岛,邂逅老顽童周伯通,意气相投,向他传授了伟大的武学原理,“双手互搏”!
谓予不信?试将二人的传记《漫游奇境记》《射雕英雄传》对照一下,就清楚了:
“有时候,爱丽丝严厉责骂自己,把自己都骂哭了。有一次,她一个人代表两方打一局槌球,因为自己捣鬼,她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这个奇怪的小孩,特别喜欢装成两个人。”
“周伯通道:‘我在桃花岛上耗了一十五年……苦在没人拆招,只好左手和右手打架。’郭靖奇道:‘左手怎能和右手打架?’周伯通道:‘我假装右手是黄老邪,左手是老顽童。右手一掌打过去,左手拆开之后还了一拳,就这样打了起来。’”
金庸要塑造一个“老顽童”形象,首先要揣摩、把握儿童心理,自己童年的阅读体验立马鲜活起来……
周伯通“双手互搏”,必有“爱丽丝漫游”的身影在。
儿童有儿童的寂寞孤独,罗大佑歌中的“童年”,“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爱丽丝、周伯通则把自己幻化成两个人,自问自答、共同嬉戏、相互取暖。
五
表面看,《侠客行》与《连城诀》风格相近,而其精神内核截然相反。《侠客行》以童心观照世界,温馨童趣,《连城诀》却像一声哀鸣,发自一个阅尽世态对人性彻底绝望的老人。
“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侠客行·后记》),莎剧中“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题材”的,好像是《第十二夜》和《错误的喜剧》。轻倩松快,风格与《侠客行》为近。《连城诀》更像《雅典的泰门》,恨世、荒凉、绝望。当时金庸心境如此恶劣,与刚过去的那场中国亘古未有的大饥荒,不能无关。
《连城诀》作于1963年,比《侠客行》早两年。两年间先后写出如此不同的两部作品,这个人,太复杂,太矛盾。
我看金庸:既老猾又童真,既慷慨又吝啬,既自私又悲悯,既开放又保守,既自负又不自信,既乐天又厌世,既豁达又执拗,……
查先生,是多彩的,多面的,多向度的,矛盾人物。
六
金庸有两部小说留有不确定的结局。《雪山飞狐》那一刀要不要砍下去确实难以决断,至于《侠客行》“石破天自是更加一片迷茫:‘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梅芳姑既然自尽,这许许多多疑问,那是谁也无法回答了”的结尾,就难免故弄玄虚之嫌了。二人相貌相似到父母都分不出来,已经巧合到极点,再加上其他各种偶然因素全汇集到二人身上,还要怀疑二人是否兄弟,这也太具有严格的学术精神了。
“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把这种感情写得真切感人,作者先要有真切的感受。金庸1965年创作此书,当时长子查传侠8岁,次子查传倜3岁,性格均未定型,不过“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以金庸之明敏,对二子的天性以及各自未来的发展,应该心中有数。
查传侠不是石中玉,查传倜更不是石破天,略微有些相似而已。查传侠很“另类”,长到十一二岁,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大苦,了无意味,金庸称许长子“深刻早慧”。查传倜倒有几分痴气,说自己从小善忘,经常丢失手机,提款忘记取钱,跟石破天略微有些相似。
金庸把自己对二子寄寓的父爱,必然投射到石清身上。“他回头向石破天瞧了一眼,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要,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这恐怕也是普天下身为人父者的共同心曲。金庸在《侠客行·后记》中写道:“一九七五年冬天……我曾引过石清在庙中向佛像祷祝的一段话。此番重校旧稿,眼泪又滴湿了这段文字”,为何伤感至此?此节文字写于1977年,前一年,金庸长子查传侠自杀……
当然,金庸也会念及自身的父母当年对自己的娇宠。母亲他从来没有忘却无时不放在心里。对父亲,一则人子对“父爱”本来就不及对“母爱”感受深刻,金庸情况又比较特殊,他不是不想念父亲,是不敢想,怕敢去撕裂心灵旧日的创口。1951年,金庸的父亲被枪杀。查枢卿是海宁乡绅,心地纯厚,对人客气而随意,在金庸看来,“他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这就是金庸认为父亲做生意不精明的缘由,换个角度看,查老先生比金庸侠气更重,更“四海”,更爱朋友,更乐于助人,然而……
14年过去,痛定思痛,也许金庸的心境稍许平静了。他就会想到父亲怕他成日在家读书有碍健康拉着他出外放风筝,自己八岁那年父亲每天把报纸上连载的《荒江女侠》裁减、粘贴给自己看,想到父亲对自己的许诺,“你表哥徐志摩在剑桥留学,长大后你也到剑桥”。更多地想到“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我一本狄更斯的《圣诞述异》……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得翻来读几段……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狄更斯写作《圣诞颂歌》,对自己的一项要求就是“情节简单明了,能让孩子读懂”,此书也不妨当儿童文学作品看。
《侠客行》谈不到“伟大”,仍不失为一个温暖宽厚的心灵所写的一卷温馨蕴藉的书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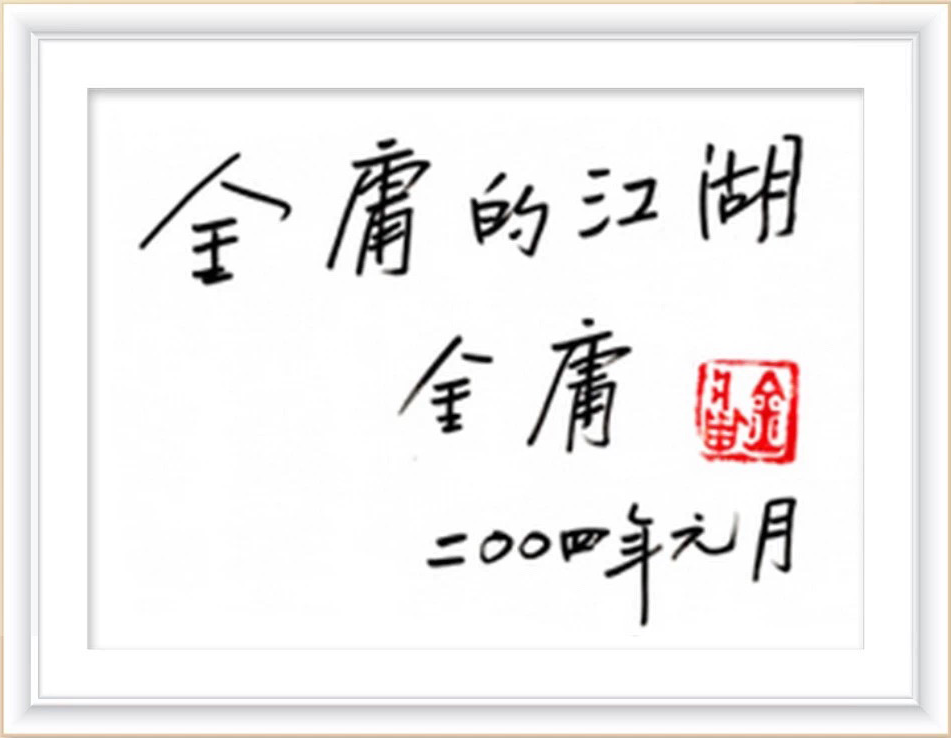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