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庸小说研究而引起的争论,无疑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剔除那些商业炒作的痕迹和意气用事的语言,仔细分析这些争论文章,就会发现,虽然评的是金庸小说,根本差别还是在于学术观念和学术风格上。本文将这些问题归纳如下,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通俗小说就是低档次、低品位的小说吗?
平心而论,批评金庸小说的人并不否定金庸小说的可读性,并且认为"金庸小说的出现,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但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 但是,"武侠小说的低档次、低品位毕竟是金庸先生的致命伤。" "说到底,金庸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文化快餐',仍然深深打上了商业文化的印记。" 意思很清楚,金庸小说再好也是通俗小说,也是武侠小说,通俗小说及其武侠小说本身就是低档次和低品位的小说,所以金庸小说也就是低档次、低品位的小说。我暂且不论这样的逻辑推论是否合理,我要问的是通俗小说(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的重要文类)就是低档次、低品位吗?
通俗小说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标准,但学术界基本认同以下的说法:它是表现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具有说故事、讲情节等传统小说的表现技巧的小说文类。根据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论定通俗小说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小说。中国传统小说确实有很多陈旧、落后的东西,当年众多的新文学家对此已经有了很多切中肯綮的批判。问题在于通俗小说有没有高档次、高品位的作品呢?我认为是有的。理由有二:
一是通俗小说自有它不可取代的道德传统和美学优势。通俗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除暴安良、因果报应、慈悲为怀、尊老爱幼、赤胆心肠……中国这些传统的道德文化确实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更多的作为优良的道德标准融化于中国人的是非判断和行为规范之中了,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道德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改良。试想一下,将这些道德文化都否定掉,中国社会又将是怎样一个社会呢?"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在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从来就是并举的,当今中国社会强调"八荣八耻",也就是做人要讲究道德。通俗小说追求消闲、娱乐和趣味,可读性强是它的文本特色。其实作为小说就应该有可读性,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严肃小说(这个名称并不科学,由于找不到更好的词汇,姑妄称之)的放弃,反而成为了通俗小说的专利。这里,我不得不提出一个敏感的话题。严肃小说对小说可读性的放弃确实与"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对"鸳鸯蝴蝶派"批判中疏忽有关。"五四"新文学作家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非常必要,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但是新文学作家采用的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没有肯定"鸳鸯蝴蝶派"文学有着很强的可读性。其实,这种疏忽带来的后果在20世纪30年代有些新文学作家就已经有所反思。30年代初瞿秋白就曾深有感触地说:"社会上的所谓文艺读物之中,新式小说究竟占什么位置呢?他实在亦只有新式知识阶级才来读他。固然,这种新式知识阶级的读者社会比以前是扩大了,而且还会有更加扩大些的可能。然而,比较旧式白话小说的读者起来,那就差得多了。一般社会不能容纳这种新式小说,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内容--他们连读都没有读过,根本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他们实在认为他是外国文的书籍。" 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有所感而发的。
二是通俗小说不断地调整和丰富自我的美学内涵,使之时时适应于社会时尚。通俗小说的市场性很强。小说的市场性很容易是作品流于庸俗化和模式化,这是通俗小说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是优秀的通俗小说往往利用市场性的特点向一些新型文学文类和艺术门类学习,不断地更新自我的美学内涵。例如,"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是"记账式"的描写法, 这的确说到到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美学弱点。优秀的通俗小说家很快地就作了调整,他们向新小说学习改变了这种缺点,代表作品可数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就举武侠小说为例吧,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我看来,20世纪武侠小说就经历三次大的变革,一次是20年代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的出现,它把武侠小说从侠义社会引入了江湖世界。第二次是40年代朱贞木《七杀碑》的出现,它把武侠小说引入进历史,将江湖和江山联系起来;第三次就是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它们把武侠小说带到了文化的空间,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艺术内涵。这三次变革,武侠小说似乎离现实生活远了,但武侠人物的主体空间凸现了出来,人性的刻画更深刻了;写的内容似乎神乎其神了,但武侠世界的空间打开了,武侠小说的美表现得更充分了。武侠小说能够这样变化,有武侠小说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武侠小说向新小说、电影艺术、外国现代小说学习借鉴的结果。
通俗小说(当然包括武侠小说)与严肃小说只不过是美学表现各有侧重的小说类型(这种区别在当今的文学界越来越模糊),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交融,又互为推动,都是当今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它们之间就不应该也不可能作什么高低之分。就像严肃小说有低档次、低品位和高档次、高品位的作品一样,通俗小说也有低档次、低品位和高档次、高品位的作品。就因为金庸小说是通俗小说,也就成为了低档次、低品位的作品,这是怎么也说不通的。
金庸小说能进入文学史吗?
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解决两大前提,一是武侠小说的美学定位,二是建立什么样的文学史观。
如果用现实主义的原则评判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确实不合情理,有在峡谷生活十几年情态不变之人吗?起码也应该是一个白毛女了;有身居山洞几十年而体格健壮者吗?起码也应得个关节炎;有喝蛇血就功力大增吗?搞的不好会被寄生虫感染;至于坐在冰山上就能飘洋过海更是荒诞不忌……根据这样的思路推演下去,武侠小说简直就是胡说八道。问题在于武侠小说恰恰不是现实主义的,它应该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不追求环境的真实性,而追求环境的奇异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不追求细节的合理性,而追求人物的行动举止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创作风格不追求冷静和客观,而追求想象力的丰富和瑰丽的色彩。从这样的思路出发,我们对武侠小说写的那些奇景、奇境就会有合理的理解,对武侠人物很多怪异的行动就会有欣赏的眼光,就会对武侠小说的想象力有一种平常的心态。我非常赞成严家炎先生的观点:"写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一些要求,对于同样是'严肃文学'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或其他现实主义的作品来说就未必合适。使用这类相对狭窄的标准,实际上当然会把不少优秀作品拒之门外。" 布用尺度,米用斗量,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应该用不同的批评标准衡量,这是进行文学批评的基本出发点。
用浪漫主义的视角评判金庸小说,金庸小说无疑是杰作。对此严家炎先生曾有精彩的论述。他认为金庸"早年用超拔的想象力创作了许多浪漫主义的武侠小说,中期以后,还用象征寓意的方法写了一批内涵更加深沉、意蕴更加丰富的作品……这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态度,也伴随着新的创作方法的采用,更多地体现在中后期的作品中。" 这样评判相当地到位。我要补充的是,中后期金庸小说的象征寓意不仅是社会、思想层面的思考上,而且上升为人性、文化层面的思考上。身在峡谷十几年,但忠贞的爱情始终不变,这就是可贵的人性;蜗居山洞数十年,但坚韧的意志始终不摧,这同样是值得颂扬的人性;想喝蛇血的人喝不到,不想喝蛇血的人反而能喝到,身处绝地,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人的性恶、性善的转换和反复被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些描述将人性的阐释上升到了文化的境界……浪漫的色彩、人文的情怀和文化的境界构成了金庸小说十分丰富的内涵。金庸小说不是没有缺点(任何作家、作品都有局限性),但总体上说,金庸小说的人文内涵和文化内涵的确超过了以前的同类小说,说这样的小说的出现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又有什么不对呢?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怎样编写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了,一直难以定论。在我看来,不在于文学史怎么编,而在于文学史观怎么定。现有的20世纪文学史大多是起步于50年代,完成于80年代初,调整于90年代中期。严格的说,这些文学史只能称之为"中国新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主潮文学史",而不应该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因为这些文学史的文学史观是新文学史观,它们总结和阐释的是20世纪的新文学和新文化,忽略和漠视的是大量的中国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化,它们既不能代表"现代",更不能概括"20世纪"。以这样的文学史观编史,金庸小说乃至整个通俗文学永远是没有重要地位的,即使到了90年代文学史编写的调整期的时候,有些文学史将金庸小说或通俗文学写进了史内,它们也是作为一个补充添在文学史的末尾。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建立一个消解雅俗、只论经典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的编写将是另一个天地。这样的文学史观认的是的经典作品,无论来自于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排斥的是非经典的作品,同样,无论来自于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这样的文学史并不是没有主次之分,新文化和新文学占主要地位,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占次要地位,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事实,但是主次之分决不是高低之分,更不是文本的美学特征之分。这样的文学史并不排除文学思潮之间的批评和反批评,但是它们只是一个现象的描述,而不应是文学史的结论,更不是排斥某种文学作品的理由。只有建立了这样的文学史观,金庸的小说和通俗文学才会以适当的地位进入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才能称得上是"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
金庸有必要对小说进行第三次修改吗?
这个问题曾在各种网站上热烈讨论过,金庸先生也已经进入了工作程序。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看起来只是一个作家创作自由的事情,在我看来,并不那么简单。
任何一位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尽善尽美,都想让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完美的流传下去,这大概是金庸先生高龄修改自己小说的动力。我不同意有些人将此看作为商业行为,因为,金庸先生不缺这个钱,更没有必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却不赞成金庸先生对他的小说进行第三次修改。理由是:
文学作品一旦出版发表,它就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财产,而且是社会大众共有的资产,无论是美是丑,"媳妇"已经见到"公婆"了。"她"已经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即使脸上有些"雀斑",大多数家庭成员并不以此为怪,而况金庸的"女儿"又如此受人喜爱呢?现在金庸先生重新修改的他的小说,就像给自己的"女儿"重新"描红画眉",让"她"再嫁一次。再见一次"公婆",此举大概既不尊重"公婆",也不尊重自己的"女儿"。
金庸先生修改自己的小说当然是听了读者和专家的很多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否就是正确的呢?很值得思考。例如曾被炒作得十分红火金庸先生将要修改的两个地方,我看都没有必要修改,一是《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与梅超风的关系,一是《鹿鼎记》中如何处理韦小宝7个老婆的问题。现在版本中的黄药师与梅超风关系有什么不自然呢?黄药师清高、偏执,对妻子至情至性,对女儿呵护有加,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物。梅超风是黄药师的徒弟,也是黄药师现有个性的制造者。正因为她与师兄陈玄风偷走了《九阴真经》,才出现了黄药师的妻子背书呕血而亡,才出现了黄药师逐徒闭岛等怪戾的举动。但是黄药师与梅超风毕竟是师徒关系,他们的恩怨是"家里的事",不允许别人插手,更不允许别人利用。在关键的时候,他们互相帮忙、一致对外,十分正常。令人不解的是,这么一个相当精彩又令人信服的情节却要被修改。如果真如传闻那样在他们之间加上一些爱情的作料那就更不可思议了。这就不仅要修改他们的师徒关系,还要修改黄药师与梅超风两人的本性,要修改涉及到他俩以及陈玄风等人的众多的情节。这些人物的个性和小说的情节一动,大概就不是修改小说了,而是重新创作了。韦小宝有7个老婆,大概是最招到很多人的非议的地方了。金庸先生动了修改的念头多少受到这些非议的影响。其实金庸先生大可不必理睬这些非议,更不能动修改的念头。因为这些非议说明了这些人并没有真正读懂这部小说。不管这些非议是什么说法,其出发点都是一个:这是一个陈腐的一妻多妾的模式。用现代法制的眼光单单看这个问题,似乎是这么一回事。但是《鹿鼎记》恰恰就不是一部宣扬法制、讲究道德的武侠小说,而是一部消解既有文化、消解既有道德的反武侠小说。这是自《射雕英雄传》之后金庸先生萌发出来的逆向思维、追求真我的创作思路结出的最为丰硕的果实。《鹿鼎记》嘲笑的是顾炎武等人狭隘的民族观念,嘲笑的是陈近南等人狭隘的忠义观念,嘲笑的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揭露的是顾炎武、陈近南等人思想意识中的丑陋的一面,展示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很多偶然性和非理性。《鹿鼎记》所嘲笑的正是众多的武侠小说和金庸的前期小说所歌颂的人和事情,揭露的正是众多的武侠小说和金庸前期小说所掩盖的人和事情。所以说这是一部"反武侠小说"。韦小宝有7个老婆正是这种创作思路的结果。在正宗的"武侠爱情观"中,无论是"众男追一女",还是"众女追一男";无论爱情写得多么热闹,真正的大侠都是对爱情忠贞不二的,他心中的恋人只有一个。韦小宝就不是什么大侠,而是一个讲义气、无原则的小流氓,他没有什么爱情,只有满足自我的欲望,他不是恋人一个,而是女人7个。一个小流氓做了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他娶了7个老婆,不正是对正宗的"武侠爱情观"的嘲笑和消解么?写得相当合理和精彩。试想一下真要使韦小宝象杨过那样,对爱情忠贞不二,挡住众多女性的诱惑,只娶一个老婆,那到是滑稽可笑了;再试想一下,如果小说的最后让韦小宝的7个老婆离他而去,只留下他孤身一人,以达到惩戒和教育的目的,整部小说的创作思路就不顺,思想内涵就稀薄得多。《鹿鼎记》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消解既有文化的格局。如果说康熙代表着"庙堂文化",韦小宝则代表着世俗的"亚文化",康熙对韦小宝是那么地投缘,韦小宝在"庙堂"中如鱼得水,他们看起来是君臣关系,实际上是文化关系。他们如此地融合,说明他们本来就是一种文化,所谓"庙堂文化"和"亚文化"只是人为之分,再将他们分为上下、清浊,那就更无意义了。根据这样的思路,韦小宝有7个老婆就更可以理解了,因为康熙的老婆比韦小宝还多。为什么康熙有那么多老婆就可以理解,韦小宝就不行呢?批评者还是用既有的文化眼光和道德眼光看问题,他们没有看到小说的文化意义。小说文本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这些修改只能是个别不通词句的梳理和错别字的订正,情节和人物是不能动的,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关目"更不能动,动一下,牵发全身。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更应该相信当时写作时的感觉和判断。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修改过自己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巴金、老舍、曹禺等人都修改过自己的作品。但是,学术界评判一位作家的文学地位,从来都是根据初版本说话。对巴金、老舍、曹禺是如此,对金庸先生同样如此。从学术研究和文学史评判的角度上看,金庸先生这一次大规模地修改小说,只能是参考的价值。从金庸小说的研究计,当务之急,并不是要看到金庸小说的修改本,而是要看到金庸小说最初在报刊上的连载本和金庸先生更多的创作感。这也是既是作家也是学者的金庸先生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文学批评非要讽刺挖苦么?
金庸小说当然是可以批评的,金庸小说并不是十全十美,金庸先生的举动并不是样样得当,特别是对那些令人生厌的毫无原则的吹捧应该给予及时地指出和指正。但是这些批评应该建立在学术的层面上和研究的视角中。非常可惜的是,这样的批评意见在当今的学术界并不多见。通读这些批评意见,不但不被说服,反而激起了人们对批评者的动机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呢?
首先是批评者们总是以"五四"新文化代言人的面貌出现,以一种教训人的面孔和居高临下地姿态看待他们的批评对象。在这样的批评框架下,批评者就成为了"五四"新文化的捍卫者,而金庸和那些推崇金庸小说的人就成为了"五四"新文学的对抗者。我们可以不论批评者是否能代表"五四"新文化,是否懂得"五四"新文化,就是这样的批评模式也的确令人难以接受。因为这不是从文学文本出发,而是从预设的观念出发,里面更多的是非学术因素;这不是平等的态度讨论问题,而是对立的态度俯视别人,里面更多的是打压的因素。在这样一种批评框架下,你说得再有理,别人也是难以接受的。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批评框架呢?在我看来是批评者对通俗文学和武侠小说的研究不够,面对着别人精细的文本分析,批评者们无法应对,就干脆捡起先辈们的语言,不分时代,不分对象的乱"打"一通。"打"得别人不敢也不能还手,因为他们知道,别人一还手就要还到"五四"先辈们的身上去了。这种看似居高临下的姿态实质上隐藏着知识准备的不足,板着的面孔说明的是内心的浮躁。令人遗憾的是,当别人指出他们的这些问题时,他们不加更改,反而做出这样的辩解:"没有读过,怎么能凭空批评?这道理似乎很过硬。但也未必置之四海而皆准。打个比方,没有吸过毒贩过毒的人就不能批评贩毒吸毒?没有卖过淫嫖过娼的人就不能批评卖淫嫖娼?除非谁能对这样的问题作否定的答复,那我就服他。" 读武侠小说就是"贩毒吸毒"?就是"卖淫嫖娼"?这样的类比就有些强词夺理了。
知识的准备不足还直接表现在很多问题的判断上。例如有位批评家对别人说"武侠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批评,并提出西方早就有了"骑士小说"。 这恰恰是这位批评家的判断错了,武侠文化确实是中国独有的,武侠文化及其小说恰恰就不同于"骑士小说"。中国的武侠小说与西方的骑士小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如讲究个人英雄主义,以武助人、扶弱济贫、为人仗义、不计报酬,都有涉险探宝的情节等,但是这些相通的地方都是一些表现形态上。从文化和美学内涵上说,它们是两种类型的小说。中国武侠小说宣扬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人文精神,西方的骑士小说表现的是西方基督教的宗教的观念;中国的侠客不拘小节,三教九流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属于民间世俗文化,西方的骑士有着优雅的风姿、适度的形态,是一个相对严密完整的社会阶层;中国的侠客忠于自我,恩怨相报,西方的骑士忠于国王,忠于教会;中国的侠客绝不会将女性作为崇拜的对象,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他们鄙视女性,西方的骑士总是以获取女性的欢心作为目标,以拥有美丽的情人作为完美人生的体现;中国的武侠小说展现的是中华武功,西方的骑士小说展现的是西方的剑术……它们的差别是这么大,怎么能捏在一块呢?将西方的骑士小说称之为"西方的武侠小说"那更是不伦不类了。
学术批评不是写杂文,它不需要语言尖刻、讽刺挖苦(真正优秀的杂文也不需要这样的文风),它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需要说出道理来。"有理不在于声高"说的也就是这样的道理。
如果说一些激愤之言还可以理解的话,一些批评者采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和"正题反做"的方法就很应该批评了。所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是从小说中寻找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取出来加以批评,对于其它与自己观点不符合的材料则视而不见。所谓"正题反做"就是将别人评论的观点进行反过来批评,材料还是别人的材料,例证还是别人的例证,但是他是反向思维,以取得创新的目的。例如有一位批评家批评金庸的《天龙八步》和《鹿鼎记》,既不论小说中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内涵,也不论人物塑造和小说美学特征,就抓住小说中的历史描写和爱情描写进行批评,说两部小说的历史描写是"戏说历史"和"篡改历史",两部小说的爱情描写是"完全陈腐不堪的一妻一妾、一妻多妾的'齐人之福'的现代版。" 任何一种美都是协调的美,是完整的美,将局部的东西从整体中拆开,再美的东西也都不美了。其实,就看他对这两部小说的两个局部的评论,也可以看出他没有真正读懂这两部小说乃至武侠小说。同样,有位批评家写了一部中国武侠小说的论著。这部论著对中国武侠小说(特别是20世纪武侠小说)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对武侠小说持肯定的态度和否定的态度都无可厚非,只要是学术的态度就可以共存。但是这部论著有些批评方法很值得推敲,相当多的论述采用的是别人的材料,别人的例证,但他却反过来说,把别人的论著作为"假想敌"进行批评。观念是很新颖,却没有什么新发现。这样的批评怎么令人信服呢?
把学术批评作为辩论词来写,那是很不当的。学术批评不是要把别人辩倒,而是要在大量的材料阅读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提高。观点摆出来,评论交给读者。"公道自有众人说"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金庸小说乃至于中国的武侠小说、通俗文学太需要文学批评了,对我国当前的文化市场、文学研究、阅读领域的发展都至关重要。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心平气和的学术研讨,而不是唇枪舌剑的辩论,更不要讽刺、挖苦的恐吓和漫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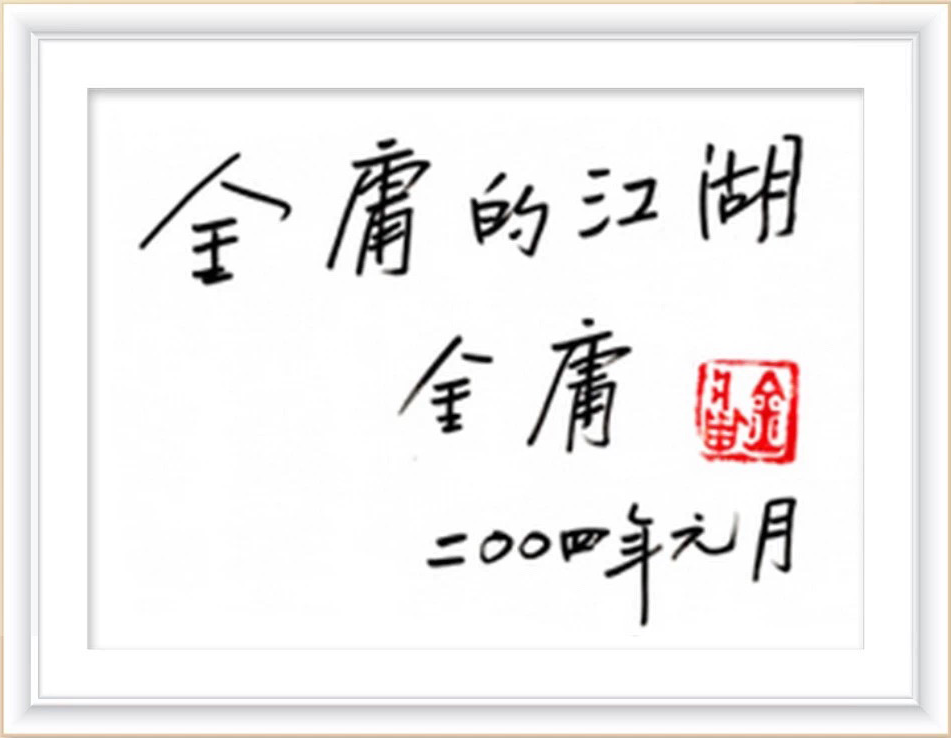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