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者以《鹿鼎记》这最后一部武侠小说追求其伟大创作理想。由继承、改造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传统和接续现代鲁迅先生对"精神胜利法"等中国国民性性格的思考,作者将从全面意义上探讨中国"历史"与"英雄"的本质关系,塑造高度浓缩具有普遍的政治性文化心理、意欲、情结与兼具"善""恶"、"正邪两赋"特征的中国国民性性格的典型形象,作为实现其伟大创作理想的重要方面。借助两极对应、"奇""正"相倚等多种创作方法,作者既以儒林清流群体"英雄"、新旧王朝帝王"英雄"、"江湖"领袖"英雄"等共同象征、表现封建社会具有崇高理想精神境界与思想情怀的"英雄",更在崇高"英雄"的映衬下,以集大成方式塑造高度凝结中国国民性性格于一身的满、汉、回、蒙、藏的"私生子"韦小宝,,将其作为中国政治性历史文化的精神产儿的典型象征。
[关键词] 《鹿鼎记》 创作动机 总体蓝图
一
关于金庸的《鹿鼎记》,如果排除连作者本人都无法预料的意外,则应如作者所说,是其创作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作者对《鹿鼎记》的基本看法,或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尽管在不同的场合和情境下,作者曾多次宣称其武侠小说创作"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不同,人物个性不同,笔法文字不同,设法尝试新的写法,要求不可重复已经写过的小说", 但作者在为修订本《鹿鼎记》所写《后记》中所强调的:"《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仍使我们意识到,作者所指《鹿鼎记》这最后一部武侠小说与其以前创作的不同,不是指以前每部作品那种不致改变其总体创作风格与形式,属于量变层次的"不断的尝试和变化",而是"故意"尝试使其具有与以前所有武侠小说完全不同的质变意义。
第二,在长期的武侠小说创作实践中,作者对历史情有独钟,在《鹿鼎记》的《后记》中,更坦承这最后一部武侠小说"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可知《鹿鼎记》创作的质变,是由于作者处理"武侠"与"历史"关系的创作方法发生了根本改变。
第三,在《鹿鼎记》的《后记》中,作者宣称若问"你以为自己哪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在其他一些访谈场合,作者也曾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并明确说"我比较喜欢最后的一部《鹿鼎记》","我的一些对文学有兴趣的朋友,多数也比较喜欢这一部。"参综来看,作者应是视《鹿鼎记》这最后一部的成就最高。
第四,《鹿鼎记》全书于1972年在《明报》连载完毕,而在十年之后所写的《后记》中,作者仍然宣称,虽然可以为"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致歉,但却要劝告、提示读者:"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并为肯定、维护自己的这最后一部武侠小说,而不惜与普通读者所抱持的"一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太过违反",可见作者高度珍视其最后一部武侠小说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作者对《鹿鼎记》的看法,为我们尝试全面探讨其深层创作动机提供了重要路径。我们知道,在创作《鹿鼎记》之前,作者早已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武侠小说创作风格,并因此而获得了远较普通作家为高的声誉。在如此情势下,还"故意"要和其以前所有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进行由"武侠"到"历史"的大胆变革,并且无怨无悔,可知在准备创作《鹿鼎记》时,作者对其以前所取得的武侠小说成就仍不满足,对其最后一部武侠小说的创作抱有更高期待。虽然作者谦虚低调,但在行将结束其创作生涯时,仍会关注其作为作家的历史定位吧?故可断言,作者对这最后一部武侠小说抱持更高期待,当与此密切相关。最后一回煞尾处的一小段文字,就透出了个中消息:"后人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为御前侍卫,曾为韦小宝的部属,后被康熙派为苏州织造,又任江宁织造,命其长驻江南繁华之地,就近寻访韦小宝云。"诚然, 作者经常虚构历史人物事迹以使小说显得更为真实,但如仅为戏拟闲笔,还非得写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吗?何况,从命名到形象塑造,韦小宝与贾宝玉显然都有较为密切的关联,而《红楼梦》正是作者所推崇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典范,作者也与主要以西方"小说"观念为指导的作家不同,是坚持继承、改造中国传统小说创作观念,"由中国人来写"全是中国的事、地方和人物的作家。尽管作者自谦不能与鲁迅等现代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坦承韦小宝形象的构思受到鲁迅《阿Q正传》的深刻影响,并对巴金、沈从文、汪曾祺、陈忠实、贾平凹等继承、改造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创作,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但客观地说,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在以中国小说观念为指导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可出现过多少差堪与贾宝玉比拟的典型形象?以具有现代精神的扬弃方式,继承、改造、反思以政治性历史文化为主创内容的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传统,是否仍然可以成为创造不朽作品的重要途径?故我们认为,作者安排曹雪芹的祖父寻访韦小宝,当不是无风兴浪,而是在含蓄暗示他对《鹿鼎记》创作的更高定位:超迈流俗与自我,使自己追步、接续曹雪芹祖父寻访中国政治文化产儿之旅,以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传统的真正继承、改造,获得与《红楼梦》作者比肩的伟大作家的历史地位。如其不然,试问作者在行将结束其武侠小说创作时的最大心事,孰过于此?确认了这一点,则作者在写《鹿鼎记》的《后记》以及接受访谈时的诸多隐约其辞、欲言又止与模糊焦点,其实就都有了答案,而其刻意的坚持与维护,也只在强调,韦小宝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独特性,是无可替代的!
二
在通常意义上,作家要形成其鲜明而独特的创作风格,殊为艰辛,有的甚且终其一生都难以实现,至于创作风格已高度成熟的作家,要进行完全的变革,风险尤大。而作者为了实现其创作理想,不惜甘冒风险,"故意"进行由"武侠"而"历史"的彻底变革。其深层原因的确值得深入探究。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当是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对现代武侠小说固有"范式"的清醒、自觉的反省意识。虽然在以前的武侠小说创作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作者也必然会感到,以"江湖"与"侠义""英雄"为基本关系模式框架的现代武侠小说创作,在表现"历史社会"与"英雄"的关系方面,疆域仍嫌狭小、模式尤易雷同:一是现代武侠小说创作虽多选择"历史"性题材内容,但其所表现的历史社会,实为以"江湖"为主导的"江湖社会",而"江湖"在以政治为主导的封建社会,总是处于边缘位置。因此,无论怎样穷形尽态,只要以"江湖社会"为主,其他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就只能仅为"江湖社会"的某种背景、侧面。这样,就无法真正从最大限度层面,有力表现更广阔、更具主导性作用的历史社会文化内容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创作主题,属于"英雄"的用武之地自然也就较为狭窄了;二是武侠小说的所谓"英雄",以"江湖""侠义"为其根本属性,而作为武侠小说主角的"江湖侠义英雄",毕竟只是"英雄"总类中的一种,并且难以与在以政治性为主导的宏大历史舞台上的政治性"英雄"相提并论,因此,或削"英雄"之"足"以适"侠义"之"履",或刻意拔高、夸大"江湖侠义英雄"的地位、作用,就成为现代武侠小说创作的习见做法;三是在一些武侠作家那里,形式表现与思想内容表现的关系严重失调、错位,所谓"侠义",往往只是以娱乐性为主创目的的"劝百讽一"之"一",在"侠义"的名义下,不厌其烦地展示"武"的功夫技巧,为大众提供惊心动魄、眩人耳目、赏心悦目的阅读效果,才是"劝百"之"百"。的确,在全面、深入、系统探讨"历史"与"英雄"文化的本质意义,全方位逼真再现古代社会的真实面貌,并塑造更为丰富、复杂、深刻、独特的典型人物形象方面,现代武侠小说创作的固有"范式",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
第二,对作者自己长期武侠小说创作实践的反思。在长期的武侠小说创作实践中,作者虽大体遵循武侠小说创作的关系模式框架与娱乐性创作传统,但其武侠小说创作的主要价值,正在于作者在"不断的尝试和变化"中,始终注重拓展、深化武侠小说的"历史"内容与"英雄"主题,并突破、超越武侠小说的一些固有表现方法,从而能够表达更多真实的、正确的社会意义以及坚定的中国精神信念,甚且呈现某种永恒的艺术价值。而随着作者对有关"历史"与"英雄"问题及其关系认识的不断丰富、深化与系统化,作者必然愈加关注、反思"历史"与"英雄"及其关系的内核与本质问题,这些关注与反思虽也会自然而然地渗透、灌注到其武侠创作中,使其后期的武侠作品在表现与"历史"、"英雄"相关的某些局部和方面,有愈多愈大的突破与超越,但与此同时,作者也必然愈加对严重制约其创作的武侠小说固有创作关系模式不满,愈加渴望、追求从根本上反拨、矫正"历史""英雄"与"江湖"、"侠义"等的主次关系。这样,一方面,如何使历史文化成为武侠小说真正主导性的"英雄"舞台,而以"江湖"为辅;如何只将"侠义"纳入全面反思、表现"英雄"问题、塑造"英雄"形象的重要方面,而不将其作为主要方面;如何追求思想蕴含与精神境界的博大精深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的高度完善,而不以最大限度地夸饰"武"的功夫技巧为能事,就成为作者"故意"变革武侠小说创作模式以实现其创作理想的重要内容,《鹿鼎记》因之而必然质变为不太像武侠小说,更像历史小说;另一方面,作者对"历史"的言说,并不与传统的历史小说那样大致保持历史的原貌,而是在追求把握"历史"的本质意义与精神的同时,仍然以虚构为主,并且在由"历史社会"与"英雄"关系所主导的新的关系模式中,使"江湖""侠义"仍然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因此,作者这最后一部武侠小说的创作,实际是要在现代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固有创作"范式"之外,尝试建构具有全面超越意义的现代武侠小说创作新"范式",以利于催生具有不朽价值的武侠小说的创作。
第三,对"历史"与"英雄"的本质关系以及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传统观念的现代继承问题的反思。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谈中,作者指出,"中国传统历史人物向与政治不可分,司马迁写《史记》中的列传,以人物为主角,居全世界第一位,没人早过《史记》,后来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也以个人为主体,但年代迟了许多。中国整体社会习惯,对政治特别重视,除了政治人物,历史书中的其他人物都被安置在比较不重要的位置,像《儒林传》《列女传》、《奸人传》虽以人为主,但都不如政治人物来得重要。"作者并且高度重视"诗言志"这一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核心命题与其他文体的源流影响关系。认为以表现政治性意欲追求与情结为主的"志",既包括感情和情绪,也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心胸怀抱、思想意志,有情感部分,也有理智部分,它不仅为诗歌创作所必需,小说创作也必须重视"言志",即应当完全表达一个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主题。将作者的话联系起来分析,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历史"以政治为主导,"中国整体社会习惯,对政治特别重视",人们所崇尚的"英雄",自然也以政治人物为主。因此,不但"历史"中的所谓"英雄",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也形成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普遍崇尚政治"英雄"的社会文化心理与情结。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文体都受到"诗言志"创作传统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也在由史官传统到稗官野史到小说观念发展成熟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情系"历史"中的政治文化内容和"英雄"主题的创作传统。古代具有重要或伟大价值的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等,多以深刻表现或反思与政治性的历史文化和"英雄"主题密切相关的内容而成功。而就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来看,一方面,以西方现代小说观念为主导是其主流创作倾向,正如作者所说:"现代一般文艺小说,似乎多少受西洋文学的影响,跟中国古典文学反而比较有距离。虽然用的是中文,写的是中国社会,但是他的技巧、思想、用语、习惯,倒是相当西化";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特定政治文化情势影响下,在现代现代小说的创作中,表现政治性"英雄"的传统创作趋于衰微,关注并深度挖掘、表现普通民众及其身上所体现的普遍性国民性性格,成为重要的创作内容,也出现了鲁迅《阿Q正传》这样具有不朽价值的代表作品。但客观地看,《阿Q正传》这部伟大作品是否就真正表现了最为普遍的中国国民性性格特征,却仍然有待深入探讨。作者就提到在创作《鹿鼎记》时,曾反复研究为他所崇仰的《阿Q正传》:"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时走访国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所以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可见,在作者看来,即便是鲁迅《阿Q正传》所表现的"精神胜利法",也未必就是真正最具普遍性代表意义的中国国民性性格特点。相比于阿Q的所谓"精神胜利法",在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普遍崇尚政治"英雄"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熏陶、影响下,最普遍的政治化心理、意欲、情结其实更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更能代表最普遍的中国国民性性格特点。而从追求真正完成中华民族现代化人格转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出发,借鉴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直面并从有机整体层面深入探讨中国式政治化"历史"与"英雄"的关系,深掘受最普遍的政治化心理、意欲、情结深刻影响的国民性性格,实际仍是现代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核心课题,也是现代小说创作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的重要创作内容。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西方小说观念占据主流的现代小说创作背景下,有关这一方面内容的创作不但被边缘化,甚至也在很大阿程度上被彻底忽略、漠视。正是对现代小说创作这种不应有的忽略与偏误的反思,促使作者在思考"必须完全表达一个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主题" ,并"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时,将从全面意义上探讨中国"历史"与"英雄"本质关系,塑造高度浓缩的具有普遍的政治性文化心理、意欲、情结的中国国民性人格的典型形象,作为实现其伟大创作理想的重要方面。
三
接下来,试论作者对特定历史时代的选择与人物形象塑造的总体构思。在《鹿鼎记》的《后记》中,作者强调"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那么,作者在追求其伟大创作理想时,为何会对"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情有独钟,并以韦小宝这样的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文化时代中,"在康熙时代的中国",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作者对"历史"与"英雄"关系的整体系统思考;作者对"历史"与"英雄"本质关系的特定认识,则使他将"在康熙时代的中国"的韦小宝,作为最能体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性文化心理、意欲、情结的中国国民性性格的典型形象。
最为直接的原初灵感,则当来自其家族"英雄"文化传统的启迪。在第一回和最后一回,作者都写入查伊璜故事。表面上看,其动机也近似于第一回自注的声称集查慎行诗句作为全书回目,仅是替祖先宣扬一下。但这种首、尾照应的特殊"宣扬"方式,的确容易让人想到,作者的"述祖德"或与其总体创作构思相关。加之第一回后面还以罕见的长注方式,详述其家族"英雄"文化传统与《鹿鼎记》创作最为直接而深密的关系,更让人联想,作者特意虚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追寻韦小宝,也许还在提示:《红楼梦》是其家族文化传统的产儿,《鹿鼎记》也受到作者家族 "英雄"文化传统的熏陶、孕育。
第一回自注追述,"在构思新作之初,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文字狱",全书也由"文字狱"写起。第一回以浓墨重彩叙写康熙初年有关《明史要略》的"文字狱"时,只捎带说到其祖先查伊璜也被牵连其中,但诱发作者以"文字狱"开篇的原初起点,却是自注所详记的家族在雍正朝所遭遇的一场著名的"文字狱"。最初在《明报》发表时称为"楔子"的标题"如此冰霜如此路",就选用诗人祖先查慎行在自身及家族遭遇"文字狱"时所咏的诗句。自注追述查家祖上门户科第甚盛,曾经"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祖先中的一位查嗣庭所遭的文字狱,牵连了整个家族和当时不少名士。这一事件给作者以最深的精神震撼,也为作者以强烈的忧患精神全面、系统、深入认知和反思"历史"与"英雄"文化的本质意义,提供了最为直接、鲜活、生动和具有高度原初启示意义的范本。
第一,作者的祖先查嗣庭、查慎行等在"文字狱"事件中大义凛然、不畏强权的铮铮风骨,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真正的"英雄"气质、品格与精神,与作者以前武侠小说中塑造的"英雄"人物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作为清代众多著名"文字狱"事件之一的当事人,查家祖先与当时"文字狱"中的儒林清流群体声气相应、血脉贯通,这就使作者能够更为直接、真切、内在地感受、体认、把握"文字狱"中包括家族祖先在内的儒林清流群体所表现的"英雄"气质、品格与精神,也启发作者将儒林清流"英雄"做为其塑造新的"英雄"类型的对象。我们知道,在以前的武侠小说创作中,由于作者还未能彻底打破和超越现代武侠小说的固有"范式",儒林清流 "英雄"群体类型在其武侠小说中甚为少见,但当作者郑重思考并刻意改变"江湖"与"历史"的主次关系,选择特定的政治化"历史"作为"英雄"的主舞台,以创作《鹿鼎记》这最后一部武侠小说时,就使儒林清流"英雄"群体类型成为其小说中的一大重要"英雄"类型。对其祖先"英雄"气质、品格与精神的认知,则直接促成了作者塑造包括其祖先典型查伊璜在内的儒林清流"英雄"群体形象的创作意愿。
第二,如作者自注所特意强调的,查慎行与其二弟等都是当时具有最先进思想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弟子。作为时代先进思想的继承者,查家祖先在"文字狱"事件中,也体现了一种博大崇高的"英雄"襟怀与境界。作者自注追述使祖先查嗣庭惨遭"文字狱"的杀身之祸,是由于他任江西考官所出的试题"维民所止",被歪曲为"维止"是暗指"雍正"两字去了头,又据说查嗣庭写有《维止录》。但"维民所止"引用《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如作者所阐释,是说"国家广大的土地,都是百姓所居住的,含有爱护人民之意"。雍正关心的是从极端政治私欲出发以暴虐维护其统治,而儒林清流则情系普天下人民的忧乐。祖先查慎行在遭逢"文字狱"时,所写的"为百草忧春雨少,替千华惜晓风多"这样感人至深的诗句,最足为其博大崇高的"英雄"襟抱与境界传神写照。作者由此而再读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当对这样富含超越升华意味的先进"英雄"思想及其襟抱与境界,更觉亲切有味,也更有会心。因此可以说,作者在小说中推崇并赋予各类杰出"英雄"代表以崇高的襟抱与境界,也当受到其家族"英雄"祖先很深的影响,作者也因此而以自豪的心情"述祖德",使象征其祖先"英雄"的查伊璜,厕身小说中具有崇高"英雄"襟抱、境界的清流代表之列。
第三,在以政治性为主导的封建社会的各类社会关系中,以封建帝王为代表的"王统"与以儒家为代表的"教统"的关系居于核心地位。如果说,在长期的武侠小说创作实践中,作者逐渐对封建"王统"与"教统"的本质关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那么,当作者以具有现代先进思想观念,又是遭逢"文字狱"惨祸的儒林清流后人的身份痛定思痛,就更容易将其现代思想观念与黄宗羲以及其祖先等所代表的当时最先进的超越性思想相融汇,从而以更为客观、理性与超越的眼光,看待封建王朝治乱的"一姓之兴亡"以及"夷夏之辨",以情系其心目中的"中国"的万民之忧乐为标准,全面、深入、系统反思包括家族祖先在内的儒林清流群体抗争满清王朝统治的悲剧,更准确把握由儒林清流所代表的封建"教统"与王统的本质关系,既充分认识儒林清流的价值及局限所在,也真正从对封建王朝兴衰灭亡的新陈代谢普遍规律的准确把握出发,正确区别、评价封建王权的一些代表人物,并进而及于对受最普遍的政治文化意欲与情结深刻影响的中国国民性性格的反思。这样,作者就以与其祖先具有直接而深密关系的、能够在最大限度意义层面包容封建社会各种政治性历史文化内容及其关系的康熙时代,作为小说表现"历史"的主舞台,以包括其祖先在内的儒林清流群体"英雄"代表象征封建社会儒家"教统",并将儒林清流群体"英雄"作为构建小说中其他各类人物关系的基本点:
一是作者以超越的眼光看到,在儒林中既有代表社会良心、正义、理想的清流群体,也有类似吴之荣那样的邪恶之徒;封建新兴王朝既多具"文字狱"式的普遍暴虐,也有抱持爱民治世理想的康、乾;明王朝以荒淫腐败亡国,其末代皇帝甚至也并非昏庸无能之徒,其后人中具有"英雄"理想的人物也并非没有可能,故作者不但将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与其祖先代表查伊璜等,塑造为具有崇高精神境界与思想情怀的儒林清流群体的理想"英雄"代表,也以康熙作为代表清王朝之兴盛的、具有"王道"理想追求的"英雄"代表,以明末公主九难作为追求崇高政治理想,能够深刻体认、反思明王朝衰亡之理的"英雄"代表;
二是构建儒林清流群体"英雄"典型为封建政治结构中"文"的代表,使其与"武"的"英雄"相配,以象征封建社会先进的"文""武""英雄"对"王道"理想的合力追求,第一回写作为儒林清流群体"英雄"之一的查伊璜与武将吴六奇的相会,就在全书中具有这种结构性的象征暗示意义;
三是由尝试探讨"武侠"小说新"范式",作者将儒林清流领袖"英雄"与"江湖"领袖构建为具有共同的崇高"英雄"理想追求的合作者,第一回写儒林清流领袖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与"江湖"领袖陈近南的相会,对全书统合"政治社会"与"江湖社会",以表现最具普遍性意义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政治性历史文化主题,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四是最为重要的是,对包括作者祖先在内的儒林清流群体"英雄"的关注与反思,是催生韦小宝形象最为直接的因素。关于这一点,下面详论。
第四,尽管包括作者祖先在内的儒林清流代表们怀有崇高"英雄"理想,但这种理想在满清王朝统治的社会现实中不但殊难获得真正成功,反而被视为反抗、取代王权的潜在力量, 横遭类似"文字狱"之类的冤案迫害与杀戮,作者由此而更深化了对封建王权统治本质的认知,也由反思儒林清流自身在知识系统、价值构建及其行动意志方面的缺陷,进而关注并深入思考历史文化中所谓"英雄"的成功及其与"英雄"理想境界、襟抱、思想情怀存在的巨大落差问题。作者看到,就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历史上获得成功的所谓帝王将相"英雄"多"善""恶"兼具,不但缺乏崇高理想,也具有各种人性缺陷,甚至在某些方面的缺陷还极为突出,他们中的一些人物,也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情势下,由普通民众而转型为所谓"英雄";而普通民众也具有根深蒂固的政治化文化心理、意欲及"英雄"观念,兼具"善""恶"人性特征。正如作者所说的:"在传统的说法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德国去一一拴套。就事实来说,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训相左的。"这种特定的观察与思考,就使作者虽继承中国古代小说表现政治性历史文化内容与主题的创作传统,却不再以帝王将相"英雄"为主,而是站在最能代表中国人的文化制高点上,在确保全书表现"英雄"的崇高思想境界与理想的同时,将创作重心放到了深刻反思与揭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小民百姓所普遍具有的政治性文化基因和"善""恶"兼具特征,才是最典型普遍的中国国民性性格。如作者所说:"我的目的是希望写得现实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上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有一些自省的意义。"正因如此,作者才以集大成方式高度凝结中国国民性特征于韦小宝之身,刻意将其塑造为满、汉、回、蒙、藏的私生子,以象征他是真正中国政治性历史文化的精神产儿:
一是作者写韦小宝只讲小义,须待他人喻以大义;只明小势,不明大势,与历史社会现实中获得成功的不少"英雄"和普通民众一样,虽有根深蒂固的政治化精神情结与意欲,却根本缺乏真正崇高的理想追求,只是将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善恶、是非标准作为其人生准则,更多以盲动的、无目的性的被动性的因缘际会,以"福气"获得其政治性人生的成功,从而使其与书中具有"英雄"理想追求的"儒林"与江湖"领袖"以及"文""武""英雄"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
二是以封建社会创业帝王"英雄"往往崛起于普通民众,历史现实中的人臣"英雄"内心每怀有潜隐的帝王梦想,甚至普通民众也可能有帝王"白日梦",作者在最大限度意义上,以多样可能性方式揭示韦小宝其人对帝王这一最高政治权位的意欲。书中既以"天下大宝曰位",暗示"小宝"与"大宝"的隐秘关系,也写他最后被康熙钦封为与象征满清王朝江山龙脉"鹿鼎山"同名的"鹿鼎公",使他本身就作为政治权位的象征;写他可以使康熙父亲顺帝及其师傅都听令于他,康熙以他为自己的化身,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教统"则期许并劝说他做开国帝王。
三是写韦小宝不武不文,其才能并不能与书中众多"英雄"人物相比, 却是康熙手下第一宠臣能臣与福将,为康熙办下七件大事,清政府官吏以他为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不论多么棘手的大事,一到他手中,立刻迎刃而解的本朝第一位英明能干大臣,书中大小事件、难题皆由韦小宝成功解决,成为写作定式。
四是作者以极限方式表现韦小宝"正""邪"两赋、"善""恶"兼具的才能及其性格特征。他既被康熙期许为可替代吴三桂的新平西王,也是康熙担心的白脸大奸臣的候选;他既可作为满清王朝的钦差大臣与吴三桂斗智斗勇并获得胜利,也是假冒的吴三桂的儿子,连他假冒的宦官名字中,也有吴三桂的"桂"字;儒林清流、天地会与前明公主均以他为反清复明的中流砥柱;他的母亲是最卑贱的妓女,但他的成功起点,则是被江湖"英雄"茅十八引导前往"英雄"成功的"得胜山",参谒"英雄"妓女梁红玉;韦小宝之"韦",取义绝不读书,只是对"韦编三绝"的最大讽刺,但其少年早成、聪明伶俐、机智横生、敢于决断,远非儒林清流人物所能及;他不学无术、拒绝文化学习,却又从市井江湖的通俗文化中受到"英雄"文化的熏陶,并在多位师傅的导引下成长;他流氓习气十足,既是吃喝嫖赌无所不通的"通吃伯",更是赌场上的"至尊宝",但除了无甚理想,其为人义气,乐于向善并顺应大势,人生出处的大关节并不含糊······
四
如前所说,作者在创作内容及主题方面,坚持继承、改造中国传统小说创作观念。而在创作方法方面,则融汇中西,丰富多彩。我们认为,就《鹿鼎记》来说,作者在展现其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时,更多考虑使用两极对应、"奇""正"相倚是最主要的两种。一是作者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普遍的两极对立统一思维特点, 以"正""邪"、"善""恶"、"阴""阳"、理想与现实、新旧王朝、教统与王统、"江湖社会"与"历史社会"、凡庸与崇高、高贵与卑下、才能与福气、知识与才能等构成众多两极对立的矛盾互补关系,使成为构建全书结构的重要方面。二是作者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奇""正"相倚、"正言若反"的创作方法,在表现顾炎武等儒林清流崇高"英雄"以及康熙、九难、陈近南等崇高"英雄"形象时,除对康熙根据历史记载中有诙谐特点,生发出他与韦小宝在某些人性缺陷方面殊有同好,让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对其他崇高英雄则主要采取了精严不苟的正笔笔法,塑造韦小宝形象则以"奇"为主,以"正"为辅。对其人性缺陷往往采取夸饰性的推其波扬其澜的"奇"笔写法,对其优点及能力,也多采取"正言若反"、婉曲暗示、蜻蜓点水、神龙不见首尾等"奇"笔法,辅之以"正"笔法。关于《鹿鼎记》表现手法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详论,这里不再赘述。
五
总括以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简单结论: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一样,作者也希望通过创作《鹿鼎记》这最后一部武侠小说来实现其伟大的创作理想;由继承中国小说创作传统和接续现代鲁迅先生《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等中国人的国民性性格的思考出发,作者站在最能代表中国人的文化制高点上,将从全面意义上探讨中国"历史"与"英雄"本质关系,塑造高度浓缩普遍的政治性文化心理、情结与兼具"善""恶"、"正邪两赋"特征的中国国民性性格的典型形象,作为实现其伟大创作理想的重要方面。就具体创作构想而言,则以两极对应、"奇""正"相倚为其主要创作方法,一方面以由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与其祖先代表查伊璜等代表儒林清流群体"英雄",以康熙与九难分别代表新旧王朝的帝王"英雄",以陈近南代表"江湖"领袖"英雄",使其共同象征封建社会具有崇高理想精神境界与思想情怀的"英雄";二是在书中崇高"英雄"的映衬下,以集大成方式塑造高度凝结中国国民性特征于一身的满、汉、回、蒙、藏的私生子韦小宝,使其真正作为中国政治性历史文化的精神产儿的典型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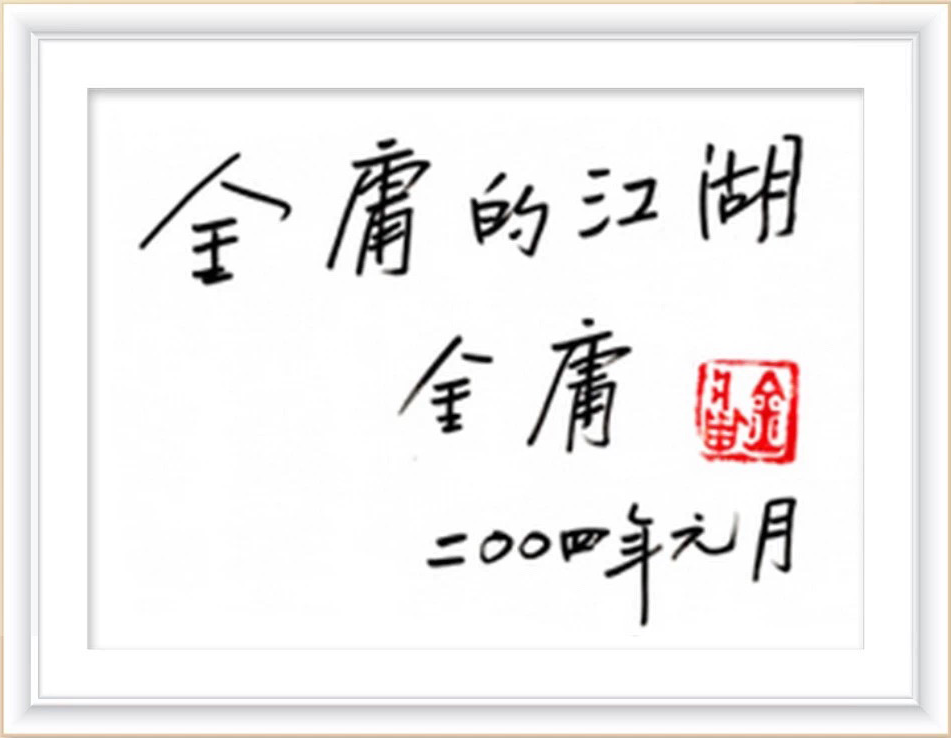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