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昙花一现到严申禁令
金庸崛起于1955年,不旋踵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在台湾,金庸作品很早就有流传,1957年,时时出版社出版了以金庸本名挂衔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三书,可以视为金庸小说进入台湾的前锋。其中,最引起读者瞩目的是《射雕英雄传》一书。金庸《射雕英雄传》于1957年开始连载于《香港商报》,立刻不胫而走,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与重视,向来认为武侠小说可以跻升文学殿堂,甚至曾发愿创作武侠小说的学者夏济安,在此书刊载不久后,即感慨地认为:“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而已故的武侠名家古龙,也曾回忆他年轻时每天清晨,鹄候在某出版社门口,等待着出版社老板请托香港友人用酱瓮裹以香港旧报纸,“偷渡”金庸《射雕英雄传》连载来台的旧事。
同时,就在《射雕英雄传》连载期间,台湾的出版社也开始以“盗版”方式,不定期地陆续刊行这部作品。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射雕英雄传》所展现的武侠魅力,如果可以依正常渠道发行,一定足以对台湾的武侠创作,引起不可忽略的影响。
然而,就在金庸小说开始发挥影响力的同时,一场悄然掩袭而至的政治禁令,以令人措手不及的方式,扼断了这可能的生机。几乎就在时时出版社印行金庸小说的同时,台湾保安司令部即以“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二条“匪酋、匪干之作品或译者及匪伪之出版物一律查禁”及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者”,对上述三书予以查禁、没收。1958~1959年,由莫愁出版社印行,署名作者绿文,题名取自梁羽生作品《萍踪侠影录》的盗版《射雕英雄传》地下出版,可视为金庸小说在台湾的第一个分水岭,也是台湾武版侠创作在突然失去奥援,不得不自行探索,而得以开展出新阶段的重要开始。
关于金庸小说遭到禁制的说法,历来论者多半指出,是由于《射雕英雄传》的书名,取自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中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一词。在当时视中共政权为洪水猛兽,举凡有一事一物相关即惹嫌疑的风声鹤唳、鸡飞狗跳的氛围中,《射雕英雄传》居然“胆敢”与“毛泽东”挂钩,自然难以在政治魔掌下超生。此说相信是可以成立的,这是因为,即使到了金庸小说得以解禁,远景出版社第一次刊行的《射雕英雄传》,为了避免嫌疑,特意改成《大漠英雄传》,但还是难逃禁令,从这一境况判断,台湾当局对此书仍不免耿耿于怀。不过,造成禁制命运的,恐怕《碧血剑》也是祸首之一,因为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中,向来将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视为“流寇”,而金庸于此书中,颇因袭大陆“农民起义英雄”的观点塑造李自成等人。所谓“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罪名,于此书更见贴切。
台湾当局的禁书政策,缺乏一套有效的政令及管理机制,不但“人治”为患,而且时松时紧。金庸的小说虽然在最初流传之际即遭禁制的命运,但起初不过和其他多数所谓“附匪”、“陷匪”的作家学者一样,尽管列名受禁,却还没有严重到被严密监控的地步,因此,在1959年之前,还是可以见到光明、合作等出版社,堂而皇之地以“金庸”本名出版他的小说。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直接侵袭到了金庸的小说。
1959年年底,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实施的“暴雨项目”,是台湾地区首度完全针对武侠小说展开查禁的一项工作,实施期间始于1959年12月31日(文号为48年12月31日(48)宪恩字第1018号代电颁发),总计查禁书目共404种。项目的内容究竟为何,至今文献犹缺,颇难查考,尚待进一步追索。不过,据1960年2月18日《中华日报》第三版刊载,警备总部于当月15~17日,于全省各地同步取缔所谓的“共匪武侠小说”,一天之内,就取缔了97种12万余册之多,许多武侠小说出租店几乎“架上无存书”,显见此一行动持续颇久。不仅如此,此波行动首要的针对对象,即可能便是金庸,据当时负责此行动的台北市警察局长潘敦义说明:
近来本市部分书店、书摊上发现有出售出租内容荒谬下流的武侠小说甚多,其中并有以匪统战书本翻印出版者,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其毒素之深,影响社会心理,危害社会安全至大。
“匪统战书本翻印”及“颠倒历史”等等,报道中明确指称为“香港匪报上连载的武侠小说”,而且这一行动的导因,实际上是因为去年(1959)香港亚洲出版社董事长张国兴、副总经理陈刘笃回台参加十月庆典时,眼见车站、街头各大小说报摊,充斥着许多盗版的武侠小说,因此向台湾当局抗议“没有尽到保护忠贞人士出版的责任,一方面为什么还容许盗印共匪小说集团的存在”。据此,金庸小说在台受盗印而广泛流传,无疑是“暴雨项目”项庄舞剑的实际剑锋所向。
自此以后,金庸小说的普遍流传暂时画下休止符,直到1980年金庸小说正式解禁,才又展现出前所未见的蓬勃气象。
禁令下的金庸小说众生相
在台湾当局的严格禁止下,金庸小说尽管未能正式发行,流传不广,但仍始终或明或暗地发挥着影响力。就实际层面而言,金庸的作品依然在地下流通着,但“金庸”这两个字,却等于是被湮灭了。从1959年开始,坊间仍然不时可以见到金庸的作品,但是为了规避当局的查禁,书商巧妙地仿照《萍踪侠影录》的故伎,以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的方式出版,截至1972年金庸洗手归隐为止,除了《白马啸西风》、《鸳鸯刀》之外,其他作品几乎都曾刊行过,而且发行的数量也不小。
大抵上,其间可以区分为前后两期,在1972年以前,流传于台湾的金庸小说,渠道多端,除了台湾的盗印之外,有些是由旅客从香港、东南亚等处携入的;而台湾的盗印,也有些直接取香港版本影印制版,既可节省印费,在查缉时也可规避刑责。附录2所列的“暴雨项目”查禁诸书,出版者多属香港出版商,基本上可依其数量判断为影印出版或海外携入者。此时,当局的查缉行动相当严密,想来也曾受过高人指点,无论书名如何变换,皆难逃一劫。1973年以后,台湾的政治气候突变,当局将心力完全投入到所谓“党外”政治书刊的监控中,无暇兼顾于武侠小说,台湾出版商遂把握住这一罅隙,大量出版各种盗版的金庸小说,其中,变易作者及书名的盗版方式最为常见,除《射雕英雄传》外,如《书剑恩仇录》(《剑客书生》)、《碧血剑》(《碧血染黄沙》)、《倚天屠龙记》(《歼情记》)、《连城诀》(《漂泊英雄传》)、《笑傲江湖》(《一剑光寒四十洲》及《独孤九剑》)、《鹿鼎记》(《小白龙》及《神武门》)等皆是;而作者题名,以“司马翎”最为常见,“古龙”、“翟迅”等偶然一用,只要不标出“金庸”之名,通常都可以苟延残喘于一时。
除了盗印诸版外,金庸小说的“伪本”,也在此一时期偶尔出现。“伪本”有两种情形,一是“纯粹伪作”,将与金庸完全无关的小说直接题为金庸的著作,以收鱼目混珠之效,如《查禁图书目录》中所列的《江湖三剑闹京华》(疑为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即为一例。不过,此类敢于标明“金庸”本名的书籍,在禁令严格实施之际,并不多见,因为没有书商胆敢冒此不讳也。反而是另一种“托名伪作”,于此时颇为流行。“托名伪作”指的是依据金庸小说的内容加以补充演述,或启其前,或继其后,或取其中人物另起炉灶,这些书多半集中于《射雕英雄传》,如《射雕前传》、《射雕后传》、《南帝段皇爷》等书即是。这些书应是香港作家所撰,可惜已难以考查名姓,台湾书商不过捡现成便宜盗印而已。
此外,台湾犹有“仿冒金庸”之作流传。“仿冒”之作,指的是暗中抄袭金庸小说中的部分或重要情节,改为己作出版,如题为欧阳生所作的《至尊刀》,取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改写,不过改换其中主要角色的名姓、关系,便俨然成一新作;而题为“古龙”(注:旧版作“温玉”)的《双流神剑》(原作《独臂双流剑》),在全书三分之一以后,全取《笑傲江湖》故事加以敷衍;其他如石天龙的《傲视武林》(取《笑傲江湖》)、幻龙的《杀人指》(杂取《神雕侠侣》)等亦然。在金庸遭禁的状况下,不肖作者蓄意抄袭,宛然以金庸小说为“武林秘籍”,欺世盗名赚稿费,居然也能风行一时,足见金庸作品之优秀,而一般读者大众对金庸原著的陌生,亦可略窥一二。
台湾当局查禁金庸小说,从1957年开始,到1979年为止,一共延续了23年,虽然时松时紧,但亦不可不谓是“雷厉风行”;诡异的是,金庸小说虽然失去了广大的一般读者市场,却在社会高层中盛行不衰,尤其是在大专院校的教授层级中,传诵不已;而台湾当局高层,如蒋经国、严家淦、孙科、宋楚瑜等政要名流,似乎也无不对金庸小说满怀兴趣、耳熟能详。金庸的小说,虽受层层压抑,但其魅力固在,迟早将如旭阳之升,划破浑沌的黑暗。
金庸小说时代之来临
严禁金庸,本是政治的运作,金庸解禁,也导因于政策的松绑。事实上,从1973年金庸以《明报》创办人名义到台湾访问,并会见了当时的高层蒋经国、严家淦时,政治嗅觉敏感的人,早已就闻到“解禁”的气味了,因此坊间于此时所大量印制的盗版丛书,当局睁只眼闭只眼,也未见多大的动作。1979年,酝酿已久的“国建会”,又盛传金庸即将成为海外嘉宾,眼疾手快的出版商,私下运作频繁,更早已安排了各种腹案,只待时机成熟,就准备一鼓作气,打响金庸这块金字招牌。
1979年9月,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在历经两年的反复陈情后,终于获得当局首肯,以“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解禁出版。朝阳日出,金庸小说的光芒,得以遍照大地,宣示着“金庸时代”的来临。
武侠小说的“金庸时代”,是经由精密设计、完美包装而呈现出来的,是文学、政治及商业三合一的缜密组合——以金庸作品的文学质素为基础,配合着政治松绑的时机,再加上一连串有计划的商业营销手法,“炮制”而成。其中,沈登恩与当时以《联合报》总编张作锦、《中国时报》总编高信疆为首的报业人士,以及以倪匡、曾昭旭为代表的文艺学术界名人,是这一个“时代”的“舵手”。
沈登恩包办整个的营销策略,先是与《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报达成默契,邀约文艺学术界名家,在两报副刊上强力刊载推介金庸作品的文章,作为前锋;紧接着,《联合报》于9月7日起连载《连城诀》,《中国时报》于9月8日起连载《倚天屠龙记》;再者,情商倪匡在短期内赶写《我看金庸小说》专书;然后,1980年10月12日,在香港《明报》刊登“等待大师”的广告,扩大影响力;最后,则分期推出皇皇巨著《金庸作品集》,完成了第一波的造势行动,也确立了金庸小说在台湾屹立不摇的地位。1986年,金庸小说的台湾版权,转签予远流出版社,袖珍本、典藏本、普及本,三管齐下,金庸小说开始走入家庭,连续数年高居书市排行榜中销售第一名的位置,武侠小说的“金庸时代”来临,也即将跨世纪地谱写出光辉灿烂的一页。
多媒体、多向度的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之从传统租书店延伸,开始步入家庭,就武侠小说发展史而言,是一次破天荒之举,尽管这未必代表武侠小说全面获得社会舆论的肯定,但是却极具象征意义。武侠小说,至少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可以具有“传家之宝”的性质的,这对有心从事通俗小说创作的人而言,自然是莫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是,在金庸小说普遍流传的推动、刺激下,通俗文学原所具有的特色——消闲娱乐,迅速扩张,在当今台湾社会五花八门的新、旧娱乐项目中,占有一席相当重要的地位。金庸小说,不仅是平面式、书面式的小说,正朝着多媒体、多向度而发展。
武侠小说的多媒体、多向度发展,从渊源而言,自然能推溯到过去的说书、戏曲表演,如《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皆在清代与说书、曲艺有相当密切的互动。近代以来,电影兴起,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中的部分情节,也在1928年首创一连开拍18集“火烧红莲寺”的纪录;而由邓公羽的《黄飞鸿正传》敷演而成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更在名演员关德兴挑梁下,缔造过高达百部的傲人成绩。台湾的武侠小说从很早开始就展现了朝多媒体发展的斐然成果:20世纪50年代,“台湾三大家”卧龙生(《飞燕惊龙》)、诸葛青云(《夺魂旗》)、司马翎(《剑神传》)的作品,就已经搬上银幕;而在1958年,漫画家叶宏甲的《诸葛四郎大战魔鬼党》(自创)、陈海虹的《小侠龙卷风》(取自墨余生《琼海腾蛟》),则开启了台湾武侠漫画的新猷,并在60年代的台湾,一枝独秀;同时,台湾50~60年代的广播节目,七点到八点的“武侠广播剧”时段,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更风靡不知多少听众。1962年,台湾电视公司开播;1969、1971年,中视、华视相继而起。1964年,第一出武侠剧《江湖一奇女》(闽南语单元剧,钟肇政编剧,陈淑芳主演)于台视制播;1970年,《红线盗》开启武侠连续剧先声;1974年,华视长达三百集的《保镖》连续剧,更形成前所未有的收视高潮。电影、漫画、广播及电视连续剧属通俗媒体,以武侠小说的“通俗性”与之结合,自然相得而益彰。事实上,也正是在通俗媒体与武侠小说的相互影响、共振下,使武侠小说拥有了更坚实肥沃的发展土壤。在这一稳固基础下,金庸小说挟着独尊的魅力,可谓集其大成。
金庸小说改拍成为电影,据资料显示,始于1958年由胡鹏编导、曹达华主演的《射雕英雄传》。其后,金庸小说开拍成电影的,约摸有50部以上,清一色为香港制作的港产影片。由于禁令的关系,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要迟到1977年由邵氏拍制、张彻导演的《射雕英雄传》,才开始获准在台湾上映。在以后的20年间,陆续开拍了30部左右,而1993年则一连6部,都普遍受到台湾观众的欢迎。综观这些影片,早期还颇忠实于金庸原著,自1990年《笑傲江湖》起,擅改原作,因而面目全非之作,大量出现,卖点只在“金庸”二字。
金庸小说改编的漫画,据传早在60年代即有《神雕侠侣》面世,但恨未见其书;1997年,东立出版社出版香港黄玉郎的《天龙八部》,其后,何志文的《雪山飞狐》、马荣成的《倚天屠龙记》陆续推出;远流出版社则自1998年起出版李志清的《射雕英雄传》、黄展鸣的《神雕侠侣》。部数虽仍不多,但颇受读者的喜爱。
金庸小说改编的连续剧,香港早在70年代就拥有大量的观众,台湾则于1983年由台视首度引入《天龙八部》,开创了台湾金庸武侠连续剧的先河。其后,无论是港产片的引进,或是台湾电视公司自拍的剧目,无一不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连带着也掀起一波波的金庸小说讨论潮。1998年,甚至有三家电视台同一时间推出《神雕侠侣》打对台的辉煌纪录。
90年代的新兴媒体——计算机游戏及网路,“金庸旋风”之裙角也多有波及。计算机武侠游戏始于1991年10月,是由精讯公司出版的《侠客英雄传》,其后陆续有各种武侠电玩推出。1993年3月,智冠科技取得金庸授权,发表了《笑傲江湖》游戏软件,正式揭开了金庸小说在计算机游戏界的一片天地。尤其是《金庸群侠传》,将金庸的14部作品融合为一体,玩家可以自己融人游戏中作各种尝试,受到空前的欢迎。
在1990年以后,新兴的网络迅速发展,武侠题材大受欢迎,而金庸小说的相关网站,更是一枝独秀。远流出版社规划的“金庸茶馆”,人潮热络,是目前叫好又叫座的金庸小说专业网站。其他大小相关网站,无虑数十个之多,可见金庸小说之魅力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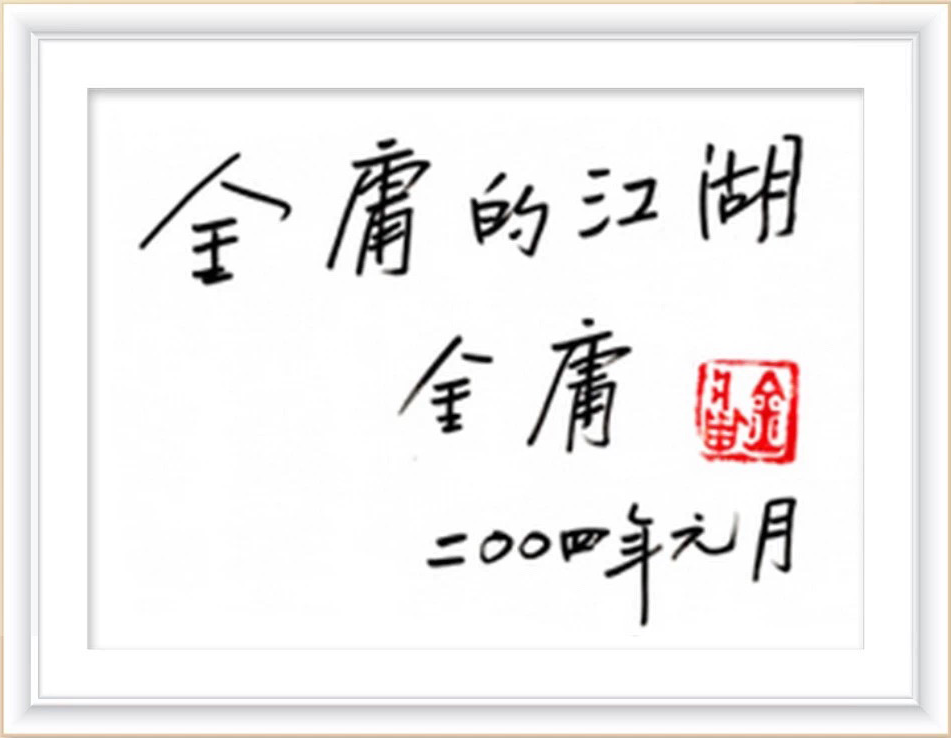


我是农民的后代 但是我仍然喜欢金庸小说和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漫画电子游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