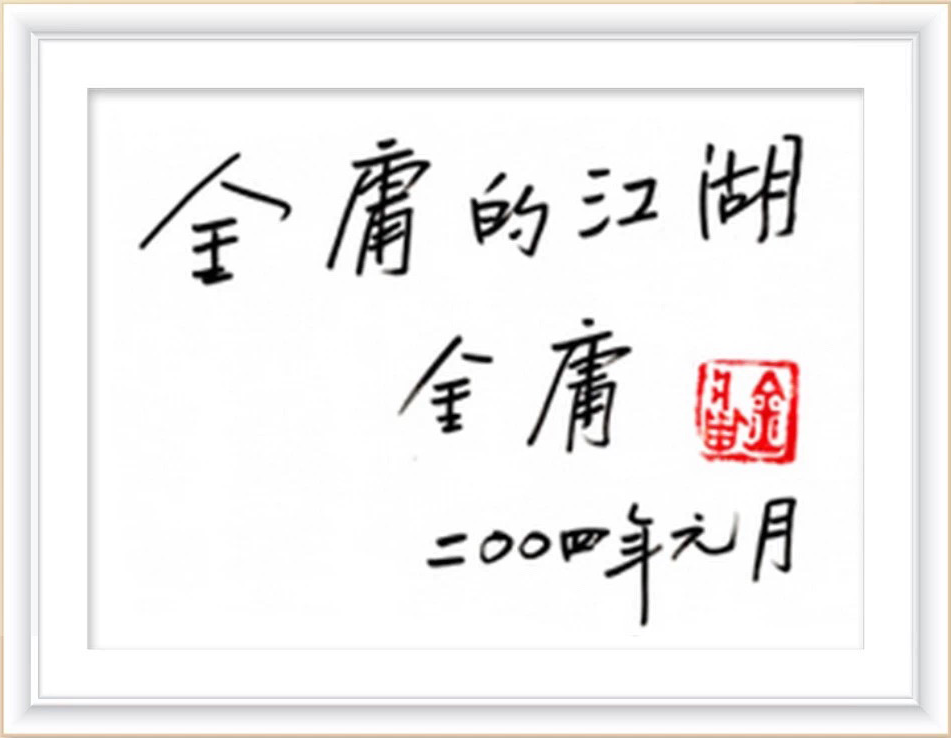金庸小说第三次修订版已经完成,尚未面世,就已经沸沸扬扬,成了近期文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又一个热点。
一、金庸小说再修改的写作行为
金庸全面修改他的小说,已经不是第一次。金庸小说从1955年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到1972年完成,跨越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岁月。1970年3月,金庸开始全面修改他的武侠小说,到1980年完成,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庸小说第二版,在大陆地区就是“三联版”《金庸作品集》。2001年,“三联版”合约到期,改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也就是在这时,传出金庸正在第三次全面修改其武侠小说的消息,一直到2007年完成。
在历史上,作品成形后再次进行修改,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就武侠小说领域而言,梁羽生、古龙都曾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但历史上的种种修改,几乎都未引起金庸小说修改这样大的争论。就古代作品而论,更多的是因为残本导致的版本学歧异而形成热点;就现代作品而论,成为热点的修改多伴随着种种文坛公案,如聂云岚与王度庐家人关于《玉娇龙》与《卧虎藏龙》的改编,如钱钟书《围城》汇校本的诉讼等等。然而,一当公案平息,修改本身已经并不构成热点。
但金庸小说的修改则不同。如果说他的上一次修改是作家对自己作品精益求精以形成“定本”的必要工作,那么这一次修改则是在金庸小说已经全面“经典化”之后貌似“重写经典”但却又未对原作进行根本颠覆的貌似“再创作”。那么,由金庸小说第三次修改,从其写作行为和文本面貌两个主要方面的背后,就可以看到更多的问题。
从其写作行为来看,其中倒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值得理解并尊重的。
在连载本时期,金庸小说虽然取得了巨大声誉,但也受到了严厉批评。在金庸小说创作开始十年之后,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对金庸小说进行了批评:一是在诗词方面闹笑话;二是武多侠少,“是非不分而消失艺术感染力”;三是团圆结局,一男多女。在梁羽生看来,“论到‘艺术水平’,新派武侠小说未必胜得过唐人的武侠传奇,甚至也未必超得过近代的白羽、还珠”[1]241-270。可以说,在连载本时期,金庸小说虽然已经名声在外,却远远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经典”。因此,全面修改以“自我经典化”,就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1980年,金庸小说在台湾远景出版修订本之后,“金学”便开始创立。然而,在1989年台湾的叶洪生所著《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中,称金庸小说为“集‘综艺’武侠之大成者”,并没有指出金庸小说的创新之处,评价也不甚高,而叶氏同时称卧龙生为“巨擘”、司马翎为“奇才”,地位在金庸之上[2]。
直到1994年,以三个事件为标志,金庸小说在大陆才开始全面“经典化”。5月,三联书店出版《金庸作品集》,被认为是金庸小说“典藏”价值的体现;10月,金庸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严家炎在致词中说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同月,海南出版社出版王一川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金庸名列第四,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1998年,更是被称为“金庸年”。至此,金庸的“自我经典化”就变成了“普遍经典化”,达到了当代作品经典化的顶峰。也正是由于金庸小说的巅峰效应,才在1999年出现了对金庸小说的文化反拨,11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王朔《我看金庸》,掀起了一股反对甚至诋毁金庸的浪潮。
在此不久之后,金庸开始了对他的小说进行再一次全面修改。这次修改,也就是在上述这样一种“誉之也极、毁之也极”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事实证明,金庸小说倾倒了无数普通读者,也倾倒了许多学者;另一方面,人们从精益求精的要求出发,也对金庸小说提出了许多质疑,包括思想意识、艺术水准以至故事细节等多个方面。由此,金庸非常重视读者和学术界的评价,自1998年以来,他参加了几乎每一次金庸小说学术研讨会,认真听取学者们的讨论。来自于读者和学者的意见,成为他修改小说的重要参照点,形成了作者、读者、学者之间的高度互动。就其具体修改情况来看,最初改《书剑恩仇录》时,人物剧情几无更动;至《碧血剑》而大开大阖;改动较多而又尤其典型的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原本透露说将在《鹿鼎记》中让韦小宝的老婆都应该“跑了才对”,但招致了读者和学者的反对,金庸本人后来也认为这样“改下去没完没了”,《鹿鼎记》和《笑傲江湖》就成了在金庸小说重要作品中修改最少的两部。
在此背景下进行的金庸小说再次修改,笔者以为,就不仅仅是金庸本人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他在表面平和的外貌掩盖之下,内心也经历了巨大的拷问与折磨,最终才下定的决心。当然,据说他在十年之后以93岁高龄还要进行第四次修改,那就有点“修改狂”的意味了。
二、金庸小说再修改的文本面貌
虽然目前还未看到金庸小说第三版的全貌,但金庸先生在修改过程中已经透露了不少情节,可以从这里进行讨论金庸小说第三版的文本面貌。
金庸小说修改的总体原则是“武功可以夸张,性格一定要真实”,落实到具体情节,则主要是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历史方面,原有的破绽要补缀,使之更连贯;二是性格方面,要更进一步反映真实人性中的复杂;三是所谓“金益求精”的小说语言,“特别改正旧版中拗口而不通顺的西式语法,并将书中部分江湖人士对话由书面语改成口语化”[3]。
就历史方面而言,金庸近些年来一直想做历史学家,并企望进入学院派的历史学,这一倾向反映到小说里,如《射雕英雄传》将“吕文焕守襄阳”一节改为“李全、杨妙真夫妇领忠义军守青州”,以符合史实,全书所涉及的地理名称、行政区域划分,也完全依照宋元时代有关文献所载,一一对应更改;《碧血剑》、《倚天屠龙记》、《鹿鼎记》也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最复杂的当然是人性问题,这一问题又集中地反映为情感问题。金庸表示:“中国传统武侠小说著眼侠义,缺少西方小说强调的情爱纠葛”,因此在新版中他要“彻底颠覆武侠的传统爱情模式”。在多部作品中,最大的修改都无异于爱情结局的颠覆,过去以团圆结局为主的模式变成了离弃和无奈,正如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金庸本人早在2003年接受采访时就说:“我在书里面写的全部是男人对女人从一而终,对她好就永远对她好。我这样写,并不是为了迎合现代,主要是觉得男主角不够‘人性’。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男性女性,一生几十年只喜欢一个人,事实上不会的。人生最理想的是拥有专一的爱情,但不专一的爱情常常有,这样改更接近现实。”[4]沿着这一思路,段誉不再执着于王语嫣,而王语嫣为了驻容有术,不惜修炼其外公丁春秋的邪功;郭襄企盼成为“大龙女”,拜金轮法王为师,而法王最后舍命救了郭襄;至于黄药师暗恋女弟子梅超风,张无忌梦想“五人行”等,更是人所熟知。
至于语言方面,1998年在美国的科罗拉多会议上,李陀提出了“金氏白话”的概念,把金庸小说的语言实践称之为“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它源自于“五四”之后的旧式白话而又极大区别于还珠楼主和张恨水,又明显地吸收了欧化的新式白话的种种语法和修辞,“正是在这种语言当中我们看到了现代汉语写作突破欧化汉语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欧化汉语和西方‘摹拟再现’这一深度模式之间的深刻联系),以追求新的更为自由解放的写作的可能性”[5]。那么,金庸小说的修改,就是通过“金益求精”而进一步提纯“金氏白话”。
三、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
金庸小说的第三次修改,背后也许有多种原因,但其中最核心的,则是从“流行经典”到“历史经典”的人为努力的轨迹。
还在20世纪末,陈洪等人就提到“经典化”相伴生的两个重要因素:“时间历程与话语权力”,并得出结论说:“《水浒传》的今天就是金庸小说的明天。”[6]陈洪等人谈到的这两个因素,笔者以为其实就是“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二者之得以形成的重要动因。
一部作品之成为“经典”,在时间之轴上,首先是拥有市场,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考验之后,得到话语权力的确认,即有可能成为“当下经典”。但往往“当局者迷”,由于作者、读者、评论者处于同一文化语境之中,三者的重复程度往往会极大相关,因此,从三个立场出发而作出的经典化评价,即自我经典化所表现的精益求精、市场经典化所表现的既畅销又长销、话语经典化所表现的进入主流文化与学术殿堂,都可能指向的是同一价值确认。这个时候,创造出来的经典,笔者称之为“流行经典”。金庸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第二版冲击自我极致、获得市场认同、进入主流学术殿堂而成为最近十余年来的“流行经典”。
“流行经典”往往具有极大的扩散效应,这也明显地表现在金庸小说“流行”的过程之中。金庸小说的扩散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庸产业的形成,包括影视、动漫、电玩等多媒体产业链延伸;二是金庸小说带来的观念延伸,集中表现为其所促进的“重写文学史”思考。
流行的深层次动力背后是技术手段所提供的大众时尚。但技术是进步着的,时尚是变化着的,技术与时尚本身都是动态发展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流行经典”,也必然就是动态的了,因此,大部分的“流行经典”都会随着时尚的变动而成为明日黄花,民国年间的武侠小说就是如此。因此,“流行经典”要保有长久生命力而成为“历史经典”,就必然要“与时俱进”地经过时间历程的考验。
“历史经典”之所以形成,和“流行经典”不同的是,“历史经典”不仅仅只是作者、读者、评者在同语境下的共同确认,更是在异语境下的共同确认。作者自我深刻化之后的回顾与修改,就是自我经典化的努力;读者在不同年代中抽取具有相对历史恒久性的价值,就是市场经典化的体现;评论者在不同文化语境和文化立场上对作品的不断重新阐释与延伸,就是话语权力经典化的工作。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努力,“历史经典”即得以形成。
金庸小说从1955年算起,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从1955年开始,分别以1970年和2001年为界,直到今天,已经形成了金庸小说自我经典化的三个历史阶段;与此同时,在中国大地之上,也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就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文化语境。也就是说,金庸小说在始终市场“流行”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具备接受不同文化语境历时考验的条件。而这就正是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的必由之路。
但问题是,金庸小说是否达到了“历史经典”的高度呢?正如本文前面所谈到,在金庸小说每一次大规模修订之前,都经历了评论界的一次巨大责难:前一次是梁羽生,后一次是王朔,他们代表的是与金庸相异的文化立场。梁羽生自称“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1]
,王朔与金庸则被学术界看作是“北京文化”和“港台文化”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及碰撞。这说明,无论连载版还是第二版的金庸小说,都还远远不足以获得异语境中的普遍价值确认。因此,对小说再次进行修改,使之兼具不同时代的文化时尚印迹,使之能够在不同文化时代都能得到流行认可,并由动态连续的“流行经典”组合而成相对固化的“历史经典”,我以为,这是金庸小说不断修改的内在动因。
金庸小说第三版的整个修改工作,事实上也是在此轨迹上进行的。其一,“金益求精”的技术手段,包括语言体系、知识准确、情节连贯等工作,这是创建“金氏白话”形成金庸小说技术原创性的经典化努力;其二,修改过程中作者、读者、学者的持续互动,这是兼顾不同文化立场与文化语境的经典化努力;其三,通过对情节结局、人物性格的修改,使结局更加符合现实情理,人物更加具有心理深度,并且在其中更好地体现出悲剧美学深度和生命美学高度,这是指向纯文学以获得“雅俗共赏”高级文化层次的经典化努力。这些不同方向的经典化努力,都共同指向了从“流行经典”到“历史经典”的蜕变。
最后,就金庸本人对于不同金庸小说版本的命运而言,他曾说过:“就像一个胖女人减肥成功了,当然希望外头流传的是她的新照片,不想再看到旧照了。”对于旧版“金迷”的抗议,金庸认为是一种“怀旧”心理[3]。因此,从金庸本人的态度而言,并不希望旧版继续流传,事实上,正如第二版修订之后,金庸已经成功地阻止了连载本的流传,现在要找到当年的连载本,几乎不大可能。当然,也已经有人提到,这对于学者的学术研究赞成了不小的障碍。但是,文学创作本身并不是为学术研究而生的,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服务对象是读者大众,其次才是学者。当然,学者的研究以及推波助澜,又会对作品的命运起到极大的作用。在作者、读者、学者之间,这是一组辩证的复杂矛盾关系。
也要注意的是,第二版和连载本不同,连载本的媒介是报纸,往往看过就扔,很难保存;第二版是书籍,已经拥有巨大的市场存量,而且,铺天盖地而来的影视、动漫,20年来使金庸进入学院体制的学术研究,依据都是第二版,这些都已经成为定型固化了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学术研究,将来的学术史回顾,都免不了要以第二版为依据。那么,金庸企图消灭第二版的存在,是否会只是一厢情愿呢?
我以为,由于版权制度的完善,金庸本人可以阻止第二版的重新出版,因为他可以不予授权。他愿意修改以及愿意哪一个版本在市场流行,这都是他的法律权力。但市场却不会因为金庸个人的意愿而牺牲大众的意愿,商业市场和学术市场都还会重新做出自己的选择。金庸也深知此点,所以他又表示,“会让旧版和新修版一起在书市上流通,使新旧读者皆大欢喜”[3]。如果说得更远一点,当将来金庸小说成为“公版”图书之后,读者的选择才是最核心的选择,而我以为那时正如现在的《水浒传》和《红楼梦》一样,金庸小说也将会具有多样化的版本系统。
那么,金庸修改小说的行为。如果说第二版还主要是改错求精,第三版就使之成了一种“现象”。其背后虽然也有商业技术和流行文化的市场动因,但核心还在于金庸自身在文化经典化需求与反拨的裹挟之下所做出的从“流行经典”到“历史经典”的努力。
而金庸小说不同版本的命运,连载本会继续湮没无闻,第二版和第三版会共同流传,其中的异同变迁,本身也会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 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G]//江堤,杨晖.金庸:中国历史大势.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241-270.
[2] 叶洪生.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53-66.
[3] 金庸十五部小说全部修改完成[EB/OL].搜房网,http://hzbbs.soufun.com/随笔人生~1007~63/5228584_5228584.htm,2006-09-01.
[4] 黄闵.金庸大改英雄谱[N].京华时报,2003-08-03(15).
[5] 李陀.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C]//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
[6] 陈洪,孙勇进.世纪回首:关于金庸作品经典化及其他[J].南开学报,1999(6):1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