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查先生,大家都知道您是《明报》的创始人,也是写武侠小说的大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您年轻时的愿望是做一名外交官。
金:我想做驻外记者的愿望是在抗战的时候产生的,我当时很想周游列国,到全世界去看看。
温:据说1950年时,你曾到新中国的外交部求过职?
金:也不是去求职,当时是外交部有个人邀请我去的。
那时候我研究的是国际公法,因为梅汝敖先生和我认识,他是当时东京战犯法庭的大法官。作为外交部的顾问,他到北京时希望有个助手,要我去,我就去了。到了以后我才发现,我将从事的工作不是在外交部,而是在人民外交学会,这和我的理想不一样,我就又回到香港继续我的新闻工作。
讲故事,是文学创作的起点。
温:您在香港呆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要选择武侠小说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
金: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武侠小说。最初,一家报纸需要一篇小说,由于兴趣所在的缘故,我自然而然就写了。中国的武侠小说看了很多,外国类似的武侠小说我也喜欢看,具有冒险性、斗争性的这类小说我都特别感兴趣。
温:您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构筑了一个具有自己道德、准则的“江湖社会”,这是否是您理想中的社会?
金: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以前的小说中就有这样的假设。比如《水浒传》这部小说,它里面描写的环境和人物,如宋江、武松……本身就是“江湖社会”中的故事和人物,当然它也有对一般人民的描写,但主要的,还是对特定的江湖社会的描写。
温:您并不会武打功夫,但您小说中所描写的情景,充分表现出您丰富的想象力和结构布局能力,这种能力您认为是训练出来的,还是天生的?
金:好像是天生的,就像讲故事,我可能会比别人讲得好一点、生动一点。企业家须有经济头脑,文人则可浪漫一点。
温: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文化人。在香港,文化人办报确实很不容易,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成功的经验。
金:文人本来是写文章的,我是新闻记者出身,但办报纸就变成一个企业家了。做企业家必须要有经济头脑,要学会计算,学会经营,这是跟文人无关的。
温:也正是因为您把“文人”和“企业家”分得清楚,才得以成功?
金:我这个脑筋可以变的。办报的同时我写两种文章,每天写一篇社评:评论政治、经济问题,有关国际政治或是内地、香港、台湾方面的问题;另一篇文章是武侠小说。
写的时候两个脑子分开。写武侠小说时不去考虑国际政治问题。
温:您写了三十多年的政论,对很多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是否也是您办报成功的一个原因?
金:恐怕报纸成功,跟我社论写得成功有关。买我的报纸,他就能看到我的一篇社评,其他的就不需要看了。
温:据说您有非常强的推测能力,您预言的很多事情在若干年后都得到了验证?
金:我比较大胆,反正这报纸是我自己办的我推测错了,也不会有人管我,也没有太大的责任。如果我拿大家的薪水,替人家做事,就不敢这样大胆,推测错了,老板要骂你了:你怎么这样乱写!
温:武侠小说和《明报》这两样东西,都为您带来了声誉和财富,武侠小说在1970年时您说不写就不写了,而《明报》也是说卖掉就卖掉了。您做事总是很决断的?
金:这些事在决定前都详细地考虑过。办报纸,人多、责任很重,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趁着我精力还好、体力还好、头脑还清醒时,早点把报纸卖掉,让适当的人来继承发展下去,这样比较合适,我应该让出来。关于武侠小说,我自己有个原则,希望不要重复:这样性格的人写过,我希望不要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写了,我希望不要重复。
我一共写了15部,很多事情都写过了,很多人物都写过了,再写下去就都重复了,读者就会觉得不好看,我自己也觉得不好看了。也可以这样说吧,已经是“江郎才尽”了,已经没有才能再创造新的故事、新的人物了。
对家乡、对祖国的依恋,是我真正的感情。
温:您生长在浙江,在重庆、上海都念过书,后来您又在香港这么多年,对香港的感情,与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相比,肯定会有所不同?
金:这种感情是不同的,我真正的感情还是对家乡、对祖国的依恋。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老了以后,回到杭州去,死在浙江。
温:能否谈谈您对香港和对故乡的感情有什么不同?
金:香港对我很好,我很多事都是在香港做的,香港给了我很丰厚的回报。我从小时候对香港很欢迎,我现在对香港也很欢迎,我做生意也很成功。我到饭馆里吃饭,很多人见到我都笑嘻嘻的,很开心,有的人会拿本书来请我签名,我觉得这是个对我很温暖的地方。我在香港得到很多东西,我希望能够对她做出回报。所以当年参加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现在又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出于这种回报的心理。有人误会,以为我想做官,希望搞政治,其实我这个人的个性不适合做官,因为我不喜欢接受命令。
温:据说当初有意邀请您来参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时,您曾经犹豫过?
金:这件事1985年开始去做。当时一直犹豫,因为《明报》是个很独立的报纸,对于内地的事情有时候批评、有时候赞美,如果我参加《基本法》起草的话,人家会说:你受了“人大”的委任,但只有赞美,没有批评了,那你就不是很独立、很公正的报纸了。当时犹豫,后来,他们向我解释,这个不是捧场,是为香港服务,希望起草一部很好的法律,为香港今后50年的发展制定一个根据。我在学校是念法律的,在这里又做了几十年的报纸,对香港非常了解,对内地也非常了解。基于这几个条件:了解内地、了解香港、又懂法律,最后就当仁不让了。我也觉得应该出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就很热心、很努力地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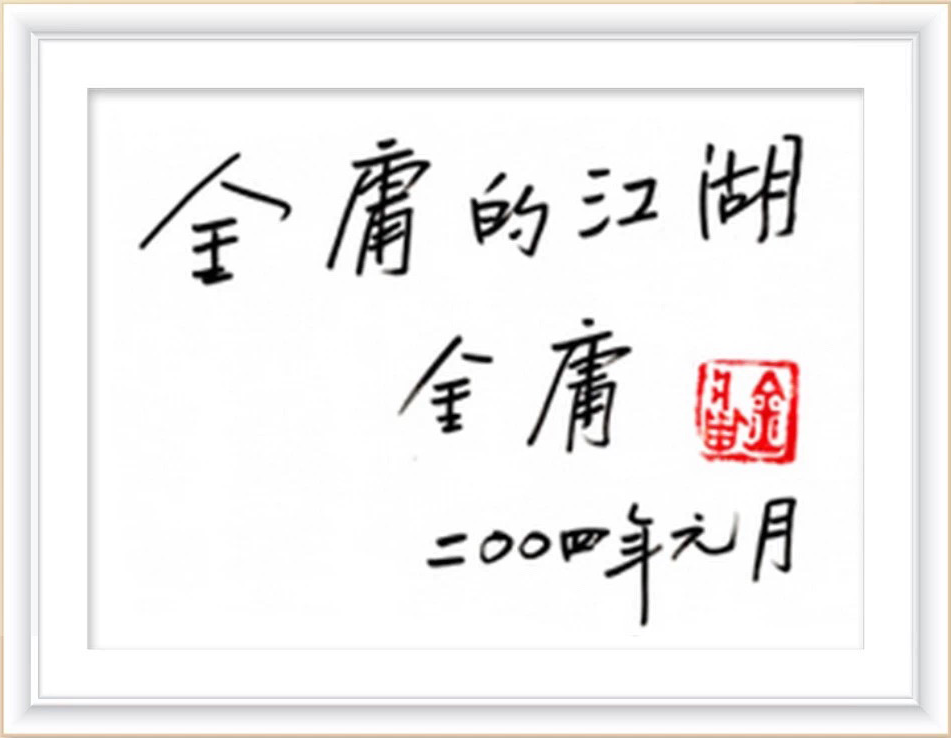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