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国学已绝数十载,目前能淹贯四部、综摄九流、总说三教者,尚无其人。 ——龚鹏程
一
钱钟书先生多次向友人们推介余英时先生的作品,友人对钱先生惊叹:“海外当推独步矣!”
不料此种论调钱先生深为不喜。钱先生回应道:“(余英时的学识)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注1】
友人推余先生“海外独步”,意念中当有海内“文化昆仑”钱钟书本人在。而钱钟书对余英时“即在中原亦为第一人”的月旦,兼有曹瞒“天下英雄,使君(刘备)与操”与欧阳修“老夫当避路,放他(苏轼)出一头地”的双重意涵,大是好玩。
2006年,余英时荣膺“克鲁格奖”,面对这份崇高的国际学术荣誉,余先生本人从容散淡,而热爱他的读者如我,仍是不自禁为之欣喜。
余英时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两年间与武侠小说家金庸多有往还,余先生自言喜欢金庸的小说,但“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
另一位国际学术大家陈世骧,则推许金庸“兄才如海,无书不读”。
“红学”大匠冯其庸初读金庸小说,更是惊佩不已一唱三叹,“这需要何等大的学问,何等大的才气,何等大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学的修养?”
需要指出的是:令余、陈、冯诸先生备致崇敬的,更多是金庸的学识而非仅指他的小说好看。
对金庸的学识、著作,董桥亦时作佳评,我有些怀疑其间或有溢美之词,毕竟董桥先后为金庸编辑《明报月刊》与《明报》十四年,评价起自己的老东家,恐不免要混杂有一份香火之情。
这个问题,在余英时、陈世骧、冯其庸身上并不存在。他们与金庸并无利害关联,据今日社会一般观感,他们学术地位、社会地位犹在金庸以上,完全没有必要违心的去恭维、吹捧金庸。
可煞作怪:余英时、陈世骧眼中“更为欣赏”的金庸“如海”学识、“文史造诣”,到了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口中,就成了“连当南大副教授都不够格”。想来董健先生的学问修养较诸余英时、陈世骧、冯其庸辈,不知要高出多少了——虽然他空前伟大的学术建树,至今仍不为世人所知。
金庸国学,究竟深浅几何?
二
金庸字写得不好,诗写得不好,词写得不好,联写得不好,古文写得尤其不好。假如这些便是国学的全部,则金庸的国学非仅不好,基本可算是不及格。
我少时嗜读金庸小说,于书中金庸自撰诗词,独赏《天龙八部》“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一语(亦舒也甚喜欢,甚至把它们用作两本书的书名),后读龚定庵诗词,方知这两句词还是窃自龚氏,“埋没了,弹指芳华如电”。其它,再无好句。
陈寅恪名作《王观堂先生挽诗》在他尊翁散原老人看来居然成了“莲花落体”之“七字唱”,对儿子,散原老人未免持论过苛。而金庸为《倚天屠龙记》所作回目,采“柏梁体”形式,那才是正宗的“莲花落”、“七字唱”,用陈寅恪好友也是金庸乡贤的王国维先生的话来说,那叫一个没境界。
金庸90年代应同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也是自己同宗长辈的查济民邀约,写了四首七律:
《参覃有感四首》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群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
京深滇闽涉关山,句酌字斟愧拙艰。
五载商略添白发,千里相从减朱颜。
论政对酒常忧国,语笑布棋偶偷闲。
钱费包张俱逝谢,手抚成法泪潸潸。
法无定法法治离,夕改朝令累卵危。
一字千金筹善法,三番四复问良规。
难言句句兼珠玉,切望条条奠固基。
叫号长街烧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
急跃狂冲抢险滩,功成一蹴古来难。
任重道远乾坤大,循序渐近天地宽。
当念万家系苦乐,敢危百姓耐饥寒。
哗众取宠浑闲事,中夜抚心可自安?
金庸“作旧诗的功力自知甚低”,从这四首诗看,不算故作谦辞。张炎评吴文英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金庸这四律,首先就不成其为楼台,句与句之间,离心力强劲,不成整体,唯见断片。俞陛云先生(俞曲园之孙、俞平伯之父、光绪24年殿试第三,真正的“老俞探花”)认为:“唐人律诗,无不气脉流通。”“大凡作律诗,忌支节横断。”金庸这四首律诗正是气脉壅滞,“支节横断”之弊显然。
1984年,金庸在京与胡耀邦先生相谈甚欢,9年后,金庸再返大陆,在威海胡先生题写的“天尽头”石碑前摄影留念,即兴题诗:“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金庸对这位难得的开明派政治家感情很深挚,可惜,诗句缺乏剪裁,不像诗,更似打油。
金庸所作对联,有一副最佳,算是神来之笔。某夜,一干好友欢聚于查(良镛)府,酒后黄霑突发奇想,跪倒林燕妮裙下求婚,林亦无意断然拒绝,于是半真半假,二人算是结缡。金庸即兴挥毫,撰联贺之:“林花沾朝露,与子偕老;黄鸟栖燕巢,共君永年。”看到这副对联,我不免联想到半个世纪前熊希龄晚年与毛彦文女士成婚时某报登出的所谓“贺联”:“熊希龄雄心不已;毛彦文茅塞顿开。”两副对联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谑而近虐,微带“情色”。——“鸟”字,我取《水浒》读法。或者,像左小祖咒所吟唱的:“阿姐有窝无鸟宿,阿哥有鸟却无窝。”
金庸所撰其他对联,均不见佳。《书剑》回目诚如梁羽生所言“偶而有一两联过得去,但大体说来,经常是连平仄也不合的”,至于他在乌镇茅盾故居所作“一代文豪写子夜;万千青年读春蚕”一联,更是浅露浮白。
若是说这就是国学的全部,则金庸的国学非仅不好,基本可算是不及格。在诗、词、联的修为上,梁羽生皆胜金庸一筹,正因为这一点,梁羽生才好意思宣称: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诗、词、联,是否就是“国学”的全部或最起码也是大部?
钱穆先生,如他自言,“好吟诗,但不能诗”。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岂不是说宾四先生的“国学”造诣远逊于梁羽生?
三
现在已经有人称呼乾隆甚至慈禧为“书法家”了,对比今日政客们的墨宝,乾隆当然高明出太多。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练字、平仄、诗词等等,是基础教育,莫说皇子,一般的读书人,无人不谙平仄诗律,无一不是诗人,也无一不是(今天标准的)书法家。
逮至清末,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逼迫这一老大帝国必须作出改变,终于,1000多年来科举取士的制度取消了,西风东渐,而旧学贬值。在耕读传家的大族中,金庸的父辈,几岁时恐怕就要进私塾,练写字、背四书、写对子、通平仄、作诗词,掌握参加科举的基本功夫,到了金庸这一代,时局丕变,这些“敲门砖”的功用已失,虽则仍有人学、做这些劳什子事,不自觉的受家庭环境影响,谙熟后,也仅仅把它们看作一种爱好,文字游戏而已。
今天有人如能写出几首合乎格律平仄的旧诗,不免自矜自喜如梁羽生者,物以稀为贵罢了。梁羽生的诗词意境不高,他掌握了一门侪辈不懂的技术,至于艺术,谈不到的。他的诗词倘能传世,要看百年后还有多少人看他的小说。小说无人看,诗词也就归于悄寂。我对梁作,印象最深的是《七剑下天山》中收录的七八首纳兰词,至于梁先生自己所撰诗词,全记不得了。
金庸身为海宁查氏子弟,查慎行的后裔,按理说他的家族应该特重旧学教育,实则不然,金庸当时接受的完全是新式教育,“五四”以后,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更进一层,旧学典籍,失去了以往的光辉。似乎当时查府颇能与时俱进,家塾早就取消了,金庸7岁进入第十七学堂就读,后转入龙山小学堂。
毕竟是文化世家,金庸家族读书的风气仍是很盛,读的却已不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竟陵桐城,而是《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等儿童读物,以及鲁迅、巴金等人的新小说,再就是读些以往被认为是“闲书”的古典小说。
对诗词曲赋,金庸“接触”的机会并不少。他的祖父查文清“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幼年的金庸近水楼台,浸淫其中,他后来在《连城诀·后记》中回忆:“(这些雕版)都成为我们堂兄弟的玩具。”至于是否读过,金庸没说,似乎没读的可能性,更大些。
1998年,在接受严家炎采访时,金庸谈到:“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
金庸早年,由于时世的变迁、家庭的忽视,根本没机会学习掌握诗词格律这门技术,不免见笑于梁羽生了。
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家,绝大多数幼年就在父兄的督导鞭笞下熟读了今天看来深奥无比而在当时仅为最低基础的各种典籍。即以无锡钱氏父子为例:钱基博5岁即从长兄习经史,九岁读完《四书》、《五经》、《古文翼》,十岁由伯父课以《史记》及唐宋八大家文选,已经开始练习写策论了。十三岁起始,通读《资治通鉴》七遍,复精读《读史方舆纪要〉。钱基博由族兄启蒙,稍不如意,即遭痛打,钱老先生居然绝无怨言,甚至告语哲嗣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教育自己的儿子,钱基博当然如法炮制。钱钟书7岁附学于亲戚家私塾,学记《诗经》,钱基博也没闲着,对钱钟书时加鞭楚。杨绛“常见锺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
无锡钱氏与海宁查氏,家风不同,但更多是时代的流转,造成金、钱二人国学根基的轩轾:钱生于1910年,长金十四岁。
至于现在五六十岁的文史学者,生长于“以俄为师”的时代氛围,受教于“破四旧”的喧嚣躁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相对隔膜,正无足怪也。我认同陈丹青的论断:“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出现大师!”
四
1937年,倭贼寇我,金庸随校南迁,千里流亡。断绝了来自家庭的经济及精神等各方面的接济,此后70年,金庸有过几次短暂的回乡之旅,至于长住海宁,再也不曾了。
离家时,金庸14岁。根植于海宁查氏数百年家族史中那份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热爱,还留存在金庸的血脉、基因里,但直接受益于家学渊源,再没有机会。
乱世求学,谈何容易!此后的金庸可以说未入名校、未遇名师。他被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录取过,却受限于经济窘困,未能赴读,他的老师中在文化上稍微有全国性影响的,是章克标先生,但章先生担任的课程,却是数学。金庸在中学阶段所写一篇考证《虬髯客传》作者的文章曾获元曲名家钱南扬先生赞许,钱先生正在该校任教,却没有直接教过金庸。这方面,金庸条件不及梁羽生远甚,梁曾受业于简又文、金应熙两位大学问家,不会毫无进益。
金庸先后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东吴大学,专业却非文史,而是外交与国际法。
至此,可以看出:金庸的旧学修养,源自家学的固少,受之于学府的亦寡。他的文史知识,泰半得诸自学。
自学,或许知识总量甚巨,但知识缺乏系统,基础有欠扎实,记忆存在盲点,做学问缺少必要的训练。科班出身的学者,未必所知甚博,但漏洞也少。一本讲义,重复讲授数十年,也尽可以应付了。
金庸文史知识的丰富,应该没有问题。余英时“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不是敷衍恭维。
说到金庸作历史学教授不够格,也非妄言,不是金庸掌握的知识不够,而是他的学术训练不足,如今的教育,不同于故往的“传道授业解惑”,事实上已经沦为(或升格为)一门技艺,这方面,金庸确实技不如人。他贸然担当历史系教授,欠妥。
近代以还,早年为诗人为小说家,后成杰出学者的,不乏其人。例如闻一多陈梦家师弟,以及沈从文先生。不过他们的转轪,是在中年,三四十岁年龄。金庸到浙大时,已经76岁,赶不及了。这一点,后来金庸本人也意识到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最想再去研究学问,当一名学者,我每次看到那些学者都很自卑,觉得自己学问不好,但是我想当初如果我不是写小说,而是去做学问的话,我一定也可以成为一名学者的。”
五
金庸1948年被《大公报》派往香港,时年25岁。当时他的同龄人(约20-30岁)中,文史根柢比金庸深的,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惜,这些人在后来的三十年中,不可能把精力主要用在商量旧学、吸纳新知上,他们根本没有地方安置自己一张小小的书桌,整个时代被“知识越多越蠢越反动”的论调所笼罩,巨量古籍被毁灭,绝大多数作品的出版遭禁绝,可供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少,偌大神州,亿兆苍生,最后就剩下了寥寥数本书可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这一代学人,独立思考既不被允许,阅读书籍的权利也遭褫夺,几十年下来,多数成就有限,泯然众人矣!
像董健这个年龄,比金庸晚一辈半辈(1948年时大约为1-18岁),情况只有更糟。金庸个人固然“未入名校、未遇名师”,而在此时,“未入名校、未遇名师”变成了整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共同悲剧。何以“未入名校”?因为我们居然可以取消高考关闭高校。虽然也有进入名校就读的,不过亲炙名师的机会依旧渺茫。若问“名师”何在?杨绛先生的追忆:“红旗开处,俞平(伯)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国家社会科学院的诸多知名学者,想必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去也?谁知不然:“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
陈寅恪先生咽气时仍有多人在旁照料逼迫老人家“交代历史问题”,吴宓先生临终饥渴交至大呼“我要喝水我是吴宓教授!”,周作人先生跪在“八道湾”户外的雨中数日,旁边有年轻人拿鞭子不断抽打……
这些老先生的大学问,及身而绝,没有或只有一二传人。多少才士的多少光阴,被旷废,被浪掷。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已经覆亡”,我总觉得有点过甚其辞,有一点,一点点……
杨继绳先生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他曾回忆道:
“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
金庸虽未遇名师,好在他自幼及老,从不缺乏阅读中西文化名著的机会,他又酷嗜读书,直到晚年“在机场候机时,他(金庸)从来不会干等,总是到处找书店看书”(《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语)。金庸每日阅读总在四小时以上,数十年下来,文化积累已是不凡。
80年代之后,一批中青年历史学者开始摒弃教条,使史学远离政治回归学术,他们的努力令人振奋甚至感动。无奈可资继承发挥的基础有限,几乎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二十年来虽说成绩不俗,但要“大成”,怕还要再二十年时间。
董健教授也并非永远没有自知之明,他在与南大学生对话时也曾坦言:
“我年轻时有过不少低潮和坎坷,1956年进大学时是俄语专业,一年后形势变化只得改学中文。之后,种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该读的书没读。因此,我这样的人是建国后高等教育煮成的夹生饭。”
董先生治学数十载,建树缺缺,不全是因为他天资有限,更多是时代原因有以促成。对此,应给与同情的理解。
董健院长之可鄙,不在他自身学问庸常反倒非议金庸学问不佳,而在于他缺乏最起码的学术品格,所谓“修辞立其诚”,学问高低不说,妄言欺世,其人的格调先就惹人怀疑。
金庸到南京大学讲演,事后,南大文学院院长的董先生面对记者口沫横飞,道是金庸讲稿错误百出金庸狼狈万状。董健教授声称当时自己是坐在主席台上,全场旁听,后来,被人揭穿:董先生的光芒并不曾照耀在主席台上。随着更多事实浮出水面,董先生改口:“当时金庸的讲演并不曾讲错什么。”
看过这些,不能不惊叹:今日学界已经与时俱进成了马戏团!
六
金庸国学,深浅几何?
那要看以何种坐标来衡量。金庸较诸章太炎、陈寅恪、钱基博、钱钟书、余英时诸大师,真正浅薄得很。
但在“国学”二字响彻云霄而“国学”水准沦落到历史最低点的今日大陆,有资格菲薄金庸的人,我看不到几个。即使不少,似乎也没这位董健先生什么事儿。
在学术界一片自我陶醉声中,北大教授郑也夫先生像童话中那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表现出惊人的坦率:
“中国学界一点不比中国足球强。老友丁学良说: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部要比北大清华都强……事情就是这样,我是学界中人,我知道双方的情况……我们的情况如何?说谁谁也不干,说自己最无妨。我觉得自己就是‘猴头巴脑’——所谓小人得志。我因何可以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呢?我古文洋文都不大通的……去年在深圳讲学一个月,才算下决心读了一遍《史记》,半部《汉书》。此前竟然是一本‘正史’也没读过。如此连中国文化人都称不上,也能做教授——完全可以说‘沐猴而冠’。但你如果说我不够教授,我也会攀比的,且振振有辞。因为我确实以为,还有好大一批教授不如鄙人。我五十岁才当教授,之前已经放弃申报了,同辈学者不论好孬,大部分在职称上比我捷足。由我推论,可信中国学术界沐猴而冠者甚多。”
旧时学人,以自己的才识赋予“教授”职衔无限荣光;今日学者,其身价亟需“教授”职务垫高。此时,一个从未当过文化部长的小说家居然捞过界,作势要分食他们的禁脔触动他们的奶酪,他们怒不可遏,不难理解。
金克木先生说金庸的“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以金克木的学问、辈份,完全有资格瞧不上金庸的佛学造诣的。但老金先生只是表示怀疑,并无董健那样的气魄,对别人一笔抹杀。
洪七公这样的高手不会彻底否定别人,裘千丈倒是曾把郭靖的武功说成毫无用处。
七
“盛世修史”,乃由戴逸领衔,从官府申请人民币六亿,打算以马列主义、毛思想,邓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撰写一部30000000字的《清史》,对此盛事,余英时先生直斥为“荒谬!”:
“以我现在了解的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来讲,合乎标准的人实在是非常少非常少,因为训练不够。如果要想找最好的清史人,中国能找到10个,20个已经不得了了……我可以断言,就是废纸。”
今日国中,真的能找出10个够水准(例如民国或海外学界的水准)的清史专家?我很怀疑。
半世纪以来,真正能站得住的历史学著作,竟有几多部?我不知道。
但,教授、学者,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对故国的文化缺乏最起码温情,拾洋祖宗唾余,眼中唯见这一条历史规律,那一个社会形态,这算哪门子历史学家?
“国学”不是记诵之学,也不是混饭吃的工具。除了葆有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对故国历史深怀温情,更要能“化”。
对故国文史,金庸从不缺乏温情,更贵在能“化”。
金庸于“文”能“化”,具见他的小说。
金庸于“史”能“化”,具见他的《明报》社论。以《资治通鉴》为范,他对当世中外情势的把握、预测,令人惊叹。
陈寅恪、王国维、钱基博诸大师不仅对典籍通透,对中国发展大势亦有深切的预知。中国文化的沦亡,传统道德的隳丧,他们早有预感。
论对典籍的把握,金庸比他们自然远为不及,但金庸对历史、现实的穿透力、预知性,并不逊色于陈王。
借用晚清学者陈澧的说法,金庸之“学”,并非“专明一艺”的“博士之学”,而是“存其大体”的“士大夫之学”。
金庸对古典文化的理性认识,远不及感性认识之深【注2】。这是他的短处,同时也正是他得天独厚的地方。
八
鲁迅嘲骂《学衡》:“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实则,吴宓等人的学养,不在鲁迅以下。鲁迅此语,想来用在我身上才恰恰好,自视实无妄谈“国学”的资格。好在看到许多“学者”放言谠论讥评他人“国学”太差,鄙人这才胆量壮大:国学啊国学,效颦阿Q质问“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追思领袖教导“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
乍着胆儿,写出此帖,通人达士纡尊垂览,一笑置之可也。
【注1】2013年,宋以朗披露,钱锺书在写给宋琪的信中,说:“余君英时之中国学问,博而兼雅,去年所晤海外学人,当推魁首,国内亦无伦比。”
【注2】金庸晚年在剑桥读博士,他的导师麦大维忆述,金庸在剑桥时和普通学生一样,每周参加研究生读书会,“有次我们讨论到一个中国古墓穴的题辞,来自北京大学及欧洲的学者都不明白,金庸就向我们解释内容,他的古文修养真是一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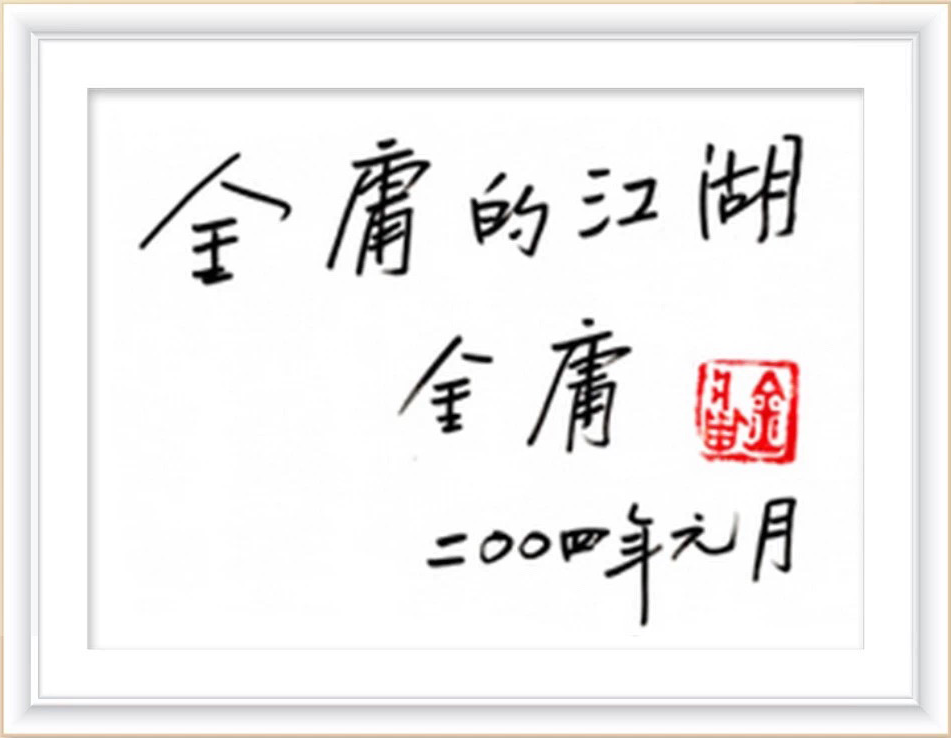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