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岁寒枝。——于右任赞张季鸾
金庸的工作经历,算是简单。一生中较长期的工作,也就两个:一是,给自己打工。从1959年创办《明报》到1994年退休,服务《明报》三十五年;之前,为老板打工。1947年进入,1958年离开,金庸为《大公报》工作十年多。金庸的《大公报》十年,对他《明报》三十五年,有奠基之功。
傅国涌先生认为金庸不是一个“伟大的报人”,这我赞同。但,面向仅1000平方公里上约四百万市民,没有哪个报人可以办出一个“伟大”的报纸,也没有哪份报纸可以成就一位“伟大”的报人。这一点,似尚非傅先生思虑之所及。
现世中找不见一个读者,一样会出伟大的文学家,只要他的作品不曾湮灭,天下后世必有识者。办报,可是与著书不同。著书可以闭门,办报总得开张。没有与分布在广阔地域的、众多的、高素质的读者的相互促成、相互激荡,“伟大报人”的出现,绝无可能。
二十世纪下半叶,香港《大公报》一直延续王芸生先生1949年为她定下的方向,其报格,比《明报》更低,而不是更高。“转向”之前的王芸生,其表现,又并不差似前辈张季鸾、胡政之。我们不能由此推论假如张、胡二先生流落到20世纪后半期的香港办报一定比金庸做得更差,但断言他们必然比金庸有更佳表现也同样不靠谱。
时势使然。张季鸾胡政之是“伟大的报人”,金庸不是,这是事实。把事实表达清楚就可以了,没必要拿一方去踩低另一方。
只有当两方处于相似的时空背景下,我们才可以以此压彼。即便将唐宋两朝地位相当的甲乙两位政治家的表现进行对比,显示出甲的高明与乙的不堪,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因为时间跨度虽大,整个社会形态却无太大改变。
20世纪前后50年太不一样了,中国一国与香港一城太不一样了。拿前五十年中面向全国办报的报人去踩低后五十年中只可以面向一座小城办报的报人,没什么意思。
金庸从他的少年时期开始,一直胸怀天下,志在天下的。有机会办一份报纸,左右举国舆论,影响国家进程,我认为他所能获得的满足感、成就感,远在多赚一倍钱以上。
何况,《大公报》又不是不赚钱:
“报馆钱越赚越多。1926年复刊时的资金是五万元,1936年创刊上海版时,报馆资财已核算为二百万元,十年间翻了四十倍。”(徐铸成《报海旧闻》)
“抗战期间,《大公报》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个地方出版,不仅都站住了,而且营业额很快就位居前位。如抗战时的《大公报》重庆版,发行高达九万多份,先后添置了十六架平板机,才得以赶印出来。当时它的发行数,几等于《中央日报》等其他九家报纸的总和。……《大公报》香港版出版后,不久发行即扶摇直上,……(桂林版)一经发行,销路就如脱缰之马,步步上升,发行数最高达六万份,也大约相当于《广西日报》、《扫荡报》等其他几家报发行之总和。”(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要论“文人办报”,金庸其实比《大公》诸子更纯粹。吴鼎昌是何等人物?入民国后历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四行储蓄会”总经理、实业部长、贵州省主席,是当日国中第一等的大财阀。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收购《大公报》,
“由吴鼎昌拿出五万元,除接盘房子、设备用去一万多元以外,全部存着作基金,准备赔上三年,……在经济上有比较可靠的准备,的确是《大公报》成功的一个条件。”(徐铸成《报海旧闻》)
金庸与同学沈宝新1959年创办《明报》时,哪有如此雄厚的资金支持?他们所能拿出的,不过自己一点可怜的私蓄。“有人说,《大公报》的成功,得力于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经营,和张季鸾的一支笔”(同上),《明报》要想成功,能靠的,只有沈宝新的经营,和金庸的一支笔。没钱!《明报》在创办之初,商业味道重了些,可以理解,未必就品格更低。
1926年,吴鼎昌拿出五万资金,实际用到的,也就两万元左右。1936年报馆资财核算为二百万元,将五万与两百万各减三万,这样算下来,《大公报》的资产在十年间翻了一百倍。它盈利增长的速度,或者还在后来者的《明报》之上。
然而,将此时《大公报》风格完全移植到金庸办报时期的香港,就行不通了,报社八成是要倒闭的。
傅国涌说“伟大的报人必须要付出,但金庸做不到,他都要得到”。1967年,金庸和他的《明报》坚决反对左 翼暴民在北平当局指使下发动的煲动,被列为第二号暗杀目标(2009年的金庸讲起“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报)的,准备给打死的”不算太夸张,而张季鸾胡政之主持《大公报》那二十年并未曾面临过如此险境),是付出;金庸数十年间经营一份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明报月刊》是“付出”;为了《明报》的长远发展,金庸没有将报纸卖给出价最高的收购者,为此损失了几亿元,更是“付出”。不,看金庸1959年后对报业的投入,得不出他要是有条件面向全国办报不能成为“伟大报人”的结论。
金庸不能成为“伟大报人”,不为他的“商业心机”,而为“政治情结”。金庸视为第一志业的,不是“办报”,是“从政”。张季鸾先生1908年在日本主编《夏声》杂志,鼓吹革命,而不入革命组织“同盟会”,因为他初入新闻界,“已决心以新闻为终生事业”(徐铸成《报人六十年》),我不认为金庸1946年进入《东南日报》当外勤记者时有同样的决心。张季鸾先生在遗嘱中自述:“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金庸对新闻事业固然很有兴趣,也有感情,却远不像季鸾先生这样专情。甚至,我怀疑金庸进入新闻界本来就有以此为跳板投身政界的打算。从清末到民国,此路一直很通。以办报起家,终成政坛大人物的,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金庸的表叔蒋百里先生1938年对记者陶菊隐就说过:“现在国家的中坚人物,哪个不是新闻记者出身?”
易代之际,金庸终于因为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有利于新朝的文章而得外交部顾问梅汝璈先生赏识,有了从政的机会。金庸没怎么犹豫,已将新闻业弃如敝屣,欣然北上求职,惜乎不顺(幸亏不顺)!仕路既阻绝,金庸这才重返《大公》,后自办《明报》。视《明报》为“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在金庸,是被逼处此,不得已也。
张季鸾与金庸易地而处,未必比金庸做得更好,金庸确有成为“伟大报人”的潜质;金庸要是在张季鸾的年代办报,却难像季鸾先生那样全始全终,尽瘁于斯,有机会他可就跳槽了。为此,唯此,金庸终与“伟大报人”无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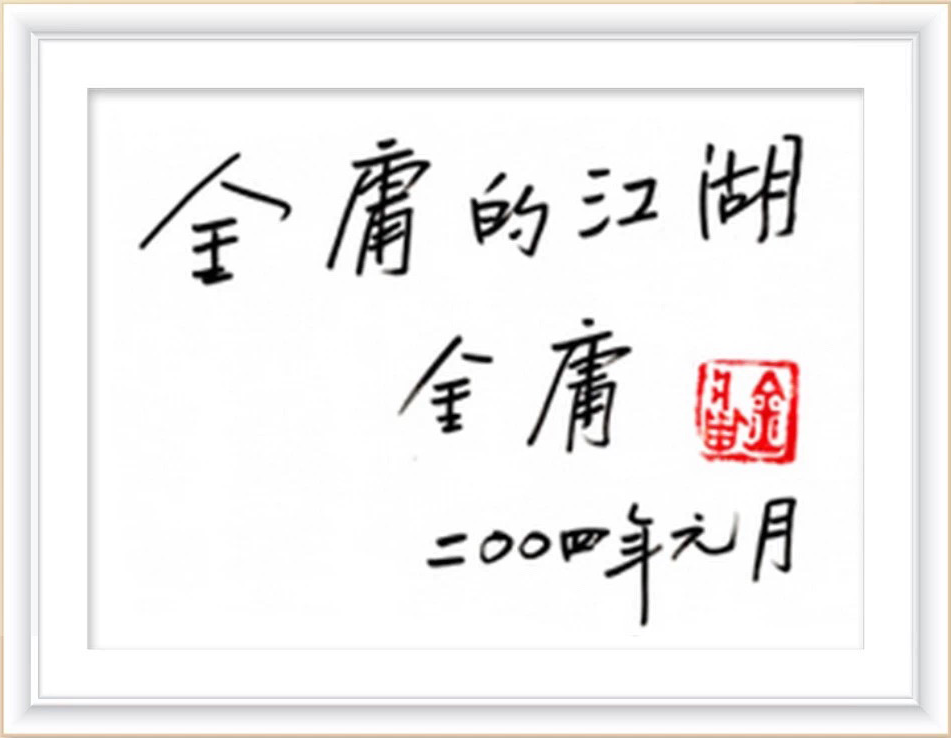


评论 (0)